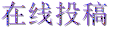钱穆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七房桥”的后代;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按照中国传统的分类法,他的学问兼涉经、史、子、集,为传统国学的通儒之学;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文、史、哲,在人文学科中当属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年,他的学生们曾这样描述他的形象:“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地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
北大学子柳存仁,曾将当年的北大教授分成了“动态”的和“静态”的两类——前者包括胡适、陈独秀等人;后者则以钱穆、孟心史为典型。“动态的教授们常常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发表一篇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的教授们则至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去搜罗旧书。……钱宾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静的方面的代表。他宁可在校内自出心裁地编著一本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作一篇西周地理考在《禹贡》上面登载,也绝不愿大张旗鼓的领导或抨击一种新的学术运动,或写一篇中华民族起源于东南沿海说。”
今天的学者,也曾将钱穆与陈寅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们二人的年龄相差不多,战争中的经历也相差不多,而且同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那是1939年的寒假,钱穆隐居在距离昆明70余千米处的宜良岩泉寺中,静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慨然而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于“静态”者中又属顶尖极的人物。
“读书人”钱穆
钱穆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地地道道的书生,心静如水的学者。他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从小学教到中学,从中学教到大学;从目光炯炯写到两眼昏花,从两眼昏花写到双目失明……他这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西南联大的风风雨雨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后方的民主浪潮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的确,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的钱穆,可谓与中华民族的忧患命运相始相终——
1904年,年仅9岁的他,第一次从果育学校钱伯圭老师那里听说了“我们的皇帝不是汉人”,听说了《三国演义》中所云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非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他“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直至晚年,他依然无比感激地说道:“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1910年,年方15岁的他,偶得谭嗣同《仁学》一书,日夜读之,手不释卷。他在文章中写道:“屡思书中言,世界人类发分四型:一全留加冠,乃中国型。全剃空头,乃印度型。剪短,乃西方型。剪前额,其余留后,垂如一豚尾,乃满洲人型。余晨起,乃一人赴理发室,命理发师剪去长辫,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翌年,辛亥革命,人人皆不留长辫,而余则已先一年去之。”
1911年的春天,钱穆转学至南京钟英中学。时值日俄战争后不久,中国处于主权丧失、领土瓜分的境地之中。每天清晨院外那“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以及腰佩刺刀街上迈步之陆军中学生”,深深地吸引住了年方16岁的钱穆,他油然而生从军之念——“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为此,他学会了骑马,并成为“每星期最主要之一门功课”。
1912年,《东方杂志》举办征文比赛,题目不限。钱穆挥毫写下《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既全面论述了英法侵犯我东南海疆、日俄霸占我北方边陲的严峻局势,告诫广大民众不可掉以轻心,又认真分析了“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他认为道路有二,一可谋和,一必交战。经过专家们的评选,钱穆的文章获得三等奖,奖金25元。
1930年,经顾颉刚的推荐,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受聘于燕京大学。他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是充满厌恶。其一:“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其二:“学校发通知,每用英文。余乃学校所聘一国文老师,无必要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办学校必发英文通知?”一年之后,钱穆即辞职他往。
钱穆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致使他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无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的“抗议”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仍在不断进行。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钱穆时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作为洋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每逢圣诞必定放假一天,但是他这位堂堂的主任,却偏偏不在布告中写上“圣诞节”三个字,只言“循例”,为的是这天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节日。
又一次是在1943年,国学研究所停办,同为教会学校的华西大学前来聘邀,钱穆没有回绝,但条件却有一个:“闻该校中国教授的宿舍均在华西坝四围附近,而西籍教授却住在坝内南端的四五栋洋楼中,条件显有高下不同。倘适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前往……”不为别的,只求:“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1932年,钱穆动笔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了,华北岌岌可危,最后竟连北平的上空亦连连出现敌国的飞机。全书完稿后,他于《自序》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斯编讲义,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为此,他大力提倡应该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坚决反对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习气与学风。
——这,便是“静态”的教授钱穆;这,便是钱穆的“爱国素不后于人”。

“教书人”钱穆
钱穆不会打仗,也从未去过前线。作为一介书生,尤其是一介以“静态”方式生活的书生,他的长项是教书,他的“武器”也是教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钱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先后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通史等一系列的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战争却残酷地破坏了这一切,故都北平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教授们精心钻研学术的书桌了。
据史料记载,1935年当日本军队阴谋策划“华北自治”时,钱穆即与姚从吾、孟心史、顾颉刚、钱玄同等100多名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条陈上下,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促请南京政府确定抗日的大计。
据北大教授罗常培回忆:“从(1937年)7月15日到月底,教职员一共在松公府大厅(现在的孑民纪念堂)集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在15日下午4时,议决通电表明态度。第二次是20日下午6时,公推钱端升、曾昭抡和我起草宣言。第三次是31日下午3时,那时北平沦陷已经三天,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静应变,共维残局。”这样的集会,钱穆全都在内。
据清华学生胡嘉回忆:“7月28日,29军宋哲元部撤离北平,我只好从清华园暂时迁进城里,住在琉璃厂北新书局,但是他们不敢存放我从清华带出的笔记、照片和讲义等。不得已装满大柳条箱,送到钱(穆)师家里,请求寄存。钱师收下了,他说:北平沦陷了,首先要设法离开这里,回到南方去。”
……就这样,为了不做亡国奴,钱穆不得不忍痛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已经工作与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校园。
对于钱穆的教学,师生们一致评价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就连著名的学者顾颉刚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至于众多的学子们,更是难以忘怀钱穆的授课风采:“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此时此刻,也正是钱穆最为陶醉的时候。他曾这样形容自己于讲课中所获得的愉悦:“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都忘记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地任性尽情地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
然而,战争却使他失去了这一切——包括熟悉的教室、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氛围、熟悉的令他“其乐无比”的心情。
钱穆的老家在苏南,他本可以挈妇将子一同回乡的,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长沙,他要去追赶自己的同事,去追赶已经在那里重新组建的“临时大学”。钱穆是于1937年的10月中旬与汤用彤、贺麟结伴上路的。行前他着实地准备了一番:在随身携带的木箱内悄悄地安装了一个夹层,外面放上几件平时穿着的衣物,里面则藏匿着他的宝贝——多年来不断补充不断修改的讲稿,足有厚厚的六大本。于是他抛妻别子匆匆上路了:由北京而天津,由天津而香港,由香港而广州,由广州而长沙……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哪知到达目的地不久,临时大学却再次搬迁了;于是再上路:由衡阳而桂林,由桂林而柳州,由柳州而南宁,由南宁而河内,由河内而昆明……
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浙江大学(遵义)、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这是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回忆——
其他大学的学生、中学的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地上坐满了,便坐到窗台上。有的人连窗台也挤不上去,便倚墙而立。常见许多同学上课时,都拿着一张报纸,为的是用以代席。这种状况,自开学以迄学年结束,始终一样,真是猗欤盛哉!
这是浙江大学学生们的感受——
文学院史地系、师范学院史地系同学全部选修,外系同学来旁听的更超过本系学生,总共一百多人,……只见宾四师目光四射,卷起衣衫,手执粉笔,开始宣讲,教材内容深入浅出。每讲一小时,起承转合,自成段落。无锡官话,声调起伏有节,忧伤激昂,其声如空谷佳音,岩瀑奔腾。举手投足,各种表情,尤引人入胜,课后有余音绕梁之感。
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产生如此的反响?——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需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墙边窗外,骈立两小时不去者复常一二十人。”——这除了他一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当年曾在西南联大听过钱穆课的何兆武这样总结道:“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这,正是钱穆作为教师的第一个特点:他将自己的激越情感、慷慨情绪,传播于、感染于在座的每一位学生,以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及民族的自信心。以他的“开场白”为例,便不同于一般的教师只是介绍课程的内容、参考的书目、考试的要求等等,而他则是一篇讲演,一篇充满激情的令人无不以自己的祖国有着如此辉煌的历史而感到骄傲与自豪的讲演。李埏这样写道:“回忆先生作此讲演时,感情是那样的奔放,声音是那样的强劲而有力,道理是那样的深切著明。那时正是国难方殷,中原陷没,学校播迁甫定,师生们皆万分悲愤之际。因此,先生的讲演,更能感人动人,异乎寻常。两个小时的课,自始至终,人皆屏息而听,以致偌大一个教室,人挤得满满的,却好像阒无一人。……我们不仅具体地、活生生地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可敬可爱之处,而且从先生讲授时所表现的、所流露的对国史的无限深情和崇高敬意,看到了榜样,感到了更大的感染力。”至于每章每节的内容,就更是如此了,无一不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史料,不饱含着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心。据吴沛澜回忆,有一次钱穆忽然将话题一下子拉到了眼前——“你们不要以为现在抗战了,就如何如何;要知道在将来的历史上,现在的这段时期是一个空白!”吴沛澜说,钱师的这番话“给我思想上以很大的震动,直到数十年后不能忘记。”是啊,这样的“震动”是为告诫在座的每一个人:抗日战争的历史将由你们自己去撰写,这段“空白”将由你们自己去填充。
钱穆授课的第二个特点,是他始终强调学以致用。严耕望是钱穆的研究生,他曾记下钱穆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在钱穆的眼中,“一流”与“二流”的区别无疑是能否为现实服务,能否影响于社会。他在对西南联大学生李埏的一番教导中,“致用”的意思就更加明确了:“学史致用有两方面,一是为己,二是为人。为己的意思,是自己受用;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矻矻,今日考这一事,明日考那一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钱穆批评了不知“为何而考”的考订家们,他自己又是如何身体力行的呢?又是如何“学以致用”于抗日战争的现实的呢?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当年他在昆明教书时,有一联大学生即赴湘鄂前线,临行前来求赠言。他点拨道:“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钱穆不是军事家,但他却断言在侵华日军当中“必有熟此书者”。因为:第一,他们在天津集兵,却不沿津浦铁路线行进,而是改道破涿州,以切断平汉线,将北平置于包围之中;第二,他们占领上海后,也不径直沿沪宁铁路线西进,而是广备船筏,直渡太湖以犯广德,从而插至南京肘腋间。此二例,皆属“攻我军之不备”,也皆属从《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获得了“要害之所在矣”。不曾想,钱穆的这一席话,竟使这部清人的著作于书肆中频频告罄,而学校方面亦一再邀请他为学生开设军事地理课程。无独有偶,当年的战地记者曹聚仁,竟然也是携带着这部《读史方舆纪要》奔波于前线的各个战区,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这就是一名谦谦学者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讲台;不是用兵器,而是用知识。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也播下了一颗又一颗蕴藏着爱国主义精神的火种。

“写书人”钱穆
作为一介书生,一介以“静态”方式生活的书生,钱穆除了教书之外,便是购书、读书、写书……他与书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他通过书感悟历史与社会,也通过书传达思想与追求。
如果没有战争的爆发,他可谓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然而,战争却让他失去了这一切——整整二十多箱的珍藏,还有他的乐趣,他的慰藉,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没有了藏书,只能去借书——颠沛流离之中,他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图书馆:在衡山,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所在地,每逢星期六的清晨,他必定要下山直奔南岳市,不为别的,那里有座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在宜良,即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的近旁,每逢星期天的下午,他必定要下山去县城,不为别的,县立中学有座图书馆,图书馆里藏有“二十五史”和“十通”……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已非同小可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一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残酷的战争同样毁掉了这一切——安静的书斋、从容的研究,代之而来的是轰炸、逃难、贫病、不安……然而,钱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提起该书的写作,钱穆总是忘不了他的同事陈梦家教授。那还是在西南联大成立后不久,文学院暂栖蒙自之时。一天陈梦家来找钱穆,鼓动他亲笔来写一部中国通史。钱穆颇感为难,一则工作量太大,二则自己所知有限,如果动笔也只能效仿清代学者赵翼所著之《二十二史札记》,“就所知者各造长篇畅论之,所知不详者付缺如。”陈梦家表示反对:“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对于有志治史学者,当受益不浅。但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此话颇令钱穆震撼,但考虑到目前尚在流亡中,他又犹豫起来:“俟他日平安返回故都再试为之吧。”陈梦家再次反对:“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耶?”就这样,这部名闻遐迩的《国史大纲》,便因“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而正式动笔了。
那是1938年的5月,钱穆开始了他的著述,“祖本”就是那批珍藏在箱子夹层中的讲义。有关这段时期的写作背景,钱穆没有留下当时的记载,但是与他同在蒙自联大文学院教书的吴宓却有日记如下:“阴雨连绵。直至6月下半月始间有晴时,7月下半月始常有晴日。而8月则全月又大雨不息矣。……而5月20日上午11:00,正对宓教室门前之大树忽倒,声如巨雷,压毙数鸟。……诚以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感。而战事消息复不佳,5月19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除了天气的郁闷、战局的危重外,更有着频繁的令人不得安宁的空袭,为此吴宓不得不深叹“人心已多悲感”,而钱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的写作。
9月,秋季开学之后,文学院迁回昆明,为了寻求安静,钱穆在宜良县的北山中觅得一寺庙“隐居”了起来,也就是后来陈寅恪来访时大呼“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的地方。其实,要说“隐居”,也并非准确,此时的钱穆仍在西南联大担负着重要的课程。为了能够将写作的时间集中,他请学校把他的课安排在周四、周五和周六的晚上。于是每到周四的中午,他便乘火车前往昆明,每到周日的早晨,再乘火车返回宜良。他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还有三个整天的时间可以关起门来写作。——1939年的6月,《国史大纲》终于完稿了!全书共计30多万字,花费了整整13个月的时间。在该书的国难版(重庆)的扉页上,钱穆写下了这样一行字: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这就是他著述的宗旨和目的:他将其视为“武器”,视为对抗战所奉献的力量。
中国史籍的编纂方法,不外乎通史与断代两种,钱穆推崇的是前者。他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因为唯有“通”,才能“积极的求出国家永久生命之泉源”,才能“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当年,是他在北大首次一人独开“通史”课;如今,又是他采用这一方法“贯通”其《国史大纲》——“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为了达到这一以古鉴今的目的,他撰写的重点也一反以往的史书多偏重于社会政治的介绍,而是将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作为三大基本内容,并从中探寻它们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国史大纲》的史学地位究竟如何?《钱穆传》的作者陈勇评述道:
《国史大纲》是钱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它是本世纪中国史坛中“最成功的史学名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程光裕语),“至今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余英时语)。该书一经出版发行,便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从内心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一位热爱自己祖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在30年代目睹日军侵凌日盛一日,终至全中华民族奋起抗战,一决存亡,而他正在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一番亲切的考察和深刻的反思;当他渊然以思、憬然以悟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将为何如?人们在这场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起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这足可见其一斑了。
抗战期间,钱穆的著作除《国史大纲》外,还有《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他自己曾经说过:以《国史大纲》为界,此前多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则转向文化研究,以复兴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无疑,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同样是源于他那对于民族前途的深刻思考——所谓民族的争存,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争存;所谓民族的力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因此要想获得抗战的胜利,必须要让广大的民众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让这一民族文化的潜力获得最为充分的发扬。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去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源,并从中培养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国人的民族向心力,重铸国人的新的民族精神。

“爱国素不后于人。”——这是钱穆曾经的誓言。他将这种“爱”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书里,融入了那一页页、一行行的文字当中。
“世内人”钱穆
进入耄耋之年后,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尤其是自1941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之多。战争结束后,他将其中有关时政方面的文章集成《政学私言》一书,并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偶得数十分钟闲,握笔排闷,隔月旬日,亦成篇幅。……检点成稿,凡获七章,其所论刊,皆涉时政,此为平生所疏,又不隶党籍,谙于实事,洛阳少年,见讥绛灌,老不知休,更可惭耻。……风林之下,难觅静枝;急湍所泻,无遇止水,率本所学,吐其胸臆。”就这样,从不过问政治的书生开始议政了,从不介入政坛的学者开始指点河山了。
钱穆“不议则已,一议惊人”,至于议论的范围,更是广泛无边:建国路线、地方自治、教育改革、法律观念、民主精神、元首制度、青年与文化、军人与文化、政治家的风度、东西方政治精神的异同……他积极地为国家献计献策,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那是1944年,日本军队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举兵进犯湘桂,顷刻间桂林、柳州失守,陪都重庆告急。在此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悲壮口号。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当年11月《大公报》上——
国事艰难,大家应该踊跃以赴。古人云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又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知识青年从军,正是俊杰识时务者之所为,这个时势是极需要英雄的了,只看英雄如何不辜负此时势。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抗战之初,西南联大有两位学生赴延安,他坚决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
……但是钱穆仍然还是钱穆,他不可能像闻一多——曾经与他同住一个教师宿舍的闻一多那样,于青天里爆出一声霹雳,于暴政下拍案而奋起。他仍然坚守着他的讲坛,仍然坚守着他的书桌,他谆谆告诫人们的也仍然是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如何能爱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作为民族生命渊源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在力量依然旺盛的表现。
——一位地地道道的书生,一位实实在在的文人,一位令世人仰慕的“国学大师”,一位“爱国素不后于人”的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