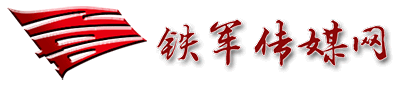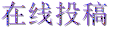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繁荣街有一条百米小巷,静静地卧在时光深处。这里流传着抗日小英雄潘鸿宝勇斗日寇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为纪念烈士,小巷被当地政府命名为“鸿宝巷”。青石板路面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每一块砖都饱含那个17岁少年的体温,每一缕微风都在传颂潘鸿宝的生命壮歌。
潘鸿宝1924年出生在小海镇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鸿宝出生不久,一家三口搬迁到小海老街的一条巷子里,买了两间茅屋安了家。
集镇市场比较繁荣,处处能目睹做生意攒下家业的人。可潘鸿宝的父母既没本钱,又不识字,不懂那些赚钱的门道,只能靠一身力气养家糊口——父亲成了码头的搬运工,母亲则在一家青货商店打零工。父亲早出晚归,小鸿宝便整天跟着母亲打转。日子虽然要靠夫妻俩起早贪黑、肩挑手扛地熬,但至少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这份平淡安稳,已让他们觉得踏实满足。
谁知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鸿宝5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躺在床上4个多月,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年仅27岁的他,丢下悲痛欲绝的母子俩。
或许是过早尝到了生活的艰苦,鸿宝从小就格外懂事。看到别家的孩子有好吃的好穿的,他从不向母亲伸手要,反而常常自己提着袋子,走街串巷地捡些废品换钱,只想替母亲多分担一点生活的重量。
到了读书的年龄,妈妈无钱供鸿宝进学堂。鸿宝就悄悄地来到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看到鸿宝求学心切,私塾周老先生动了善心,让他免费走进学堂听讲,并且送了许多旧书供他自学。《岳飞传》里“精忠报国”四个字,被他用毛笔描了又描,墨迹透过纸背,像要刻进心里。
潘鸿宝是家里的独子,却没有半点娇气。长到十三四岁时,已经是镇上出了名的“小大人”。他每天早上提着水壶去巷口的老虎灶打水,把前店的柜台擦洗得锃亮,再踮着脚帮妈妈把油罐、酱缸一一摆放整齐。顾客看到他蓝布褂的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纷纷议论:“这孩子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小鸿宝不仅舍得吃苦,还乐于助人。有年冬天,东桥口李大爷的独轮车陷在结冰的泥地里,鸿宝揣着刚热的红薯路过,二话不说扔下红薯就来推。车辙碾过石板路时,他鼻尖冻得通红,却咧着嘴笑:“大爷,下次进货喊我,我有力气。”
1940年深秋,运河里飘来一条小船,一个腿缠绷带的新四军战士被抬上岸。鸿宝立即跑回家把储备的金疮药拿来,蹲在战士身边帮他换药,受伤战士给鸿宝讲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小兄弟,鬼子占了东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赶走日本鬼子,千万不能当孬种。”那天夜里,鸿宝第一次失眠了,他回忆那名受伤战士说的话,又摸着周老先生送给他的书籍《正气歌》,手指在“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上反复摩挲。从那时起,这个爱脸红的少年,心里埋下了保家卫国的种子。
1941年盛夏,黄海之滨的暑气像团湿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8月24日清晨,东桥口的木栏刚映出第一缕晨光,西桥口突然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一艘挂着太阳旗的白色汽艇,像条巨蟒破开小海河的水面,撞向码头。
“哐当!”码头的木板被日军的皮靴踩得直颤。小队长举着军刀,刀身在晨光里闪着寒光,两个鬼子扛着黑黝黝的掷弹筒紧随其后,另几个鬼子的刺刀尖反光比毒日头更刺眼。沿街的商贩刚支起摊子,转眼就被枪托砸翻:“袁记布庄”的幌子被扯烂,油盐铺的门板被踹裂,掌柜的算盘被摔在地上,算珠滚得满地都是。
潘鸿宝攥着给母亲买的麦芽糖,躲在粮行的柱子后。他看见王婶刚染好的蓝花布被鬼子抢走,看见李爷爷的烟袋锅被踩扁在泥里,看见夏奶奶抱着孙子的棉袄蹲在地上哭……17岁的少年背靠着冰凉的柱子,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麦芽糖在汗湿的手心里化得黏糊糊的,像喉咙里堵着的那股滚烫的血。
鬼子在大街上扫荡过后,便来到码头边的饭店里狂欢,猜拳声、酒瓶碎裂声、狂笑声惊扰了半条街,惊飞了檐下的燕子。一番闹腾过后,这群鬼子带着酒气登上小汽艇离开了小海。
饭店门外有一棵老槐树,潘鸿宝骑在树枝上装着玩耍,盯着鬼子的一举一动。鬼子离开后,潘鸿宝从树上下来,突然发现饭店墙角有个黑铁筒在反光——是鬼子刚才扛着的掷弹筒!一定是鬼子把它忘在了这儿。他猛地想起游击队的高叔说过,这铁家伙挺利害,能打穿鬼子的汽艇,是战场上的“硬骨头”。
“狗东西,让你们也尝尝厉害!”潘鸿宝猫着腰窜过去,双手抱住铁筒。这玩意儿比想象中沉,可他顾不得肩膀生疼,一个劲跑得飞快,布鞋踩过巷口的水洼,向镇外东北方向芦苇荡奔去。
新四军侦察员老张接过掷弹筒时,潘鸿宝的肩膀已经红得发紫。“好小子,这可是难得的宝贝!”老张摸着铁筒上的温度,眼里闪着光,“赶快找个地方躲着,鬼子发现了要发疯的。”
可鸿宝没走。他趴在芦苇丛里,盯着镇上的烟囱。日头刚刚偏西时,那艘白色汽艇果然疯了似的冲了回来。这次鬼子的军刀上沾着血,码头边的黄狗被砍成了两半,血顺着石板缝流进小海河,染红了一大片水面。
“掷弹筒的,交出来!”日本小队长的军刀指着老包厂广场,100多个乡亲被刺刀逼成一圈。潘鸿宝看见母亲扶着崴了脚的堂哥,看见王婶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看见赵奶奶把李爷爷护在身后。鬼子把粮行的朱大叔吊在老槐树上,皮鞭抽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朱大叔却啐了口带血的唾沫:“狗娘养的,不知道!”
鬼子见大伙儿都不肯说出掷弹筒的下落,便将火把扔到广场旁边的朱子田家茅草屋上,屋顶“轰”地窜起火苗,晒在院里的芦苇噼啪作响。朱婶扑过去想抢出陪嫁的木箱,被鬼子一脚踹倒在火边,鬓角的头发燎得卷了起来。风助火势,4户人家的11间草房很快连成一片火海,黑烟裹着火星冲上天空,把日头染成了暗红色。
“不能出去!”芦苇荡里,赶来的舅舅死死拽着鸿宝的胳膊,“你娘说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话没说完,广场上突然响起枪声——鬼子朝天开枪,逼乡亲们供出掷弹筒的下落。
鸿宝看见母亲突然朝芦苇荡的方向望了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别出来”。可他想起了周先生教的“舍生取义”,想起了受伤战士说的“保家卫国”,想起了自己偷偷刻在门板上的“忠”字。他猛地挣脱舅舅的手,踩着芦苇丛里的积水冲了出去,泥水溅在粗布褂子上,身后的芦苇叶割得脖子生疼,可他跑得比刚才抱掷弹筒时更快。
“住手!”潘鸿宝站在广场中央,火光照着他挺直的脊梁。鬼子的刺刀齐刷刷对准他,他却死死盯着鬼子:“东西是我拿的,放了他们!”
水塘边的风带着腥味。潘鸿宝被麻绳捆着,手腕勒得渗出血珠。他故意放慢脚步,眼睛飞快扫过四周——这里离游击队的藏身处不远,只要再拖一会儿,张叔他们就能带着掷弹筒走远。
“快说,东西藏哪了?”牵绳的鬼子推了他一把。鸿宝突然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拽着绳子往塘里倒了下去。“扑通”、“扑通”,两人溅起巨大的水花。他一个猛子沉到水底,鬼子不会水,被呛得直翻白眼,他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意。
岸上的枪响了。子弹擦过胳膊,火辣辣地疼。潘鸿宝被拖上岸时,浑身是泥和血。鬼子小队长的军刀抵住他的脖子,刀刃冰凉:“说不说?”
潘鸿宝抬起头,夕阳落在脸上,把睫毛染成金色。“早给了新四军......”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块石头砸在鬼子心上。
汽艇驶离码头时,乡亲们涌向岸边。他们看见潘鸿宝被吊在船尾,铁丝穿透他的锁骨,血顺着铁丝滴进水里,染红了船尾的浪花。有人哭出了声,17岁的少年没有哭,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古镇,望着那片还在冒烟的屋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打......打鬼子......”
一路上,潘鸿宝早已被活活折磨死了。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仍然不甘心,傍晚到了东台二女桥,他们将已经牺牲的潘鸿宝拖上岸,在潘鸿宝身上砍了数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潘鸿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骸迁葬到大丰烈士陵园。下葬那天,镇上的人几乎都来了。李大爷推着鸿宝小时候帮他推过的独轮车,王婶抱着为他赶做的却再也穿不上的布鞋,周老先生带着私塾的孩子们,在鸿宝墓前念起了《正气歌》。
如今的鸿宝巷,墙角的青苔里还藏着当年的弹痕。放学的孩子走过这里,会听见老人说:“这里住过一个勇敢的爷爷,他用生命保护了乡亲。”阳光穿过巷口的老槐树,落在“鸿宝巷”的标牌上,熠熠生辉。
弹指一挥间84年过去了,可小巷里的炊烟依旧冉冉升起,像1941年那个清晨潘鸿宝奔跑时扬起的衣角。风穿过巷道,带着小海河的朝气,也带着少年潘鸿未说完的那句铿锵有力话语——“打鬼子”的呐喊,化作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灯光,照亮小海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前进的方向,不断茁壮成长。让革命烈士英名永存,万古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