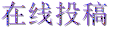特等功臣孙明芝(1926.4—2011.10)
生命奇迹
岁月流逝,父亲和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哪一天,讲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但是,父亲永远不能讲话的日子,却像刀子刻在我脑海里一样,一辈子不会忘记。
让父亲从“老家”走吧
那是2010年2月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叫小年,我们当地称为祭灶,是个传统的节日。那天是双休日,本来我是打算回沭阳陪父母吃饭的。但由于时近春节,工作比较忙,我想,反正快要过年了,这天就不回去了,等放假多陪陪老人吧。此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没想到,一语成谶,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和揪心的痛。
下午3点多钟,我接到二姐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到医院。二姐讲话声音明显发抖,带着哭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十分害怕,难道父亲这次真的……我不敢想下去了。到了医院,只见父亲躺在床上,身上打着点滴,双目紧闭,任我一遍一遍地喊,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握了握父亲的手,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这些年,父亲尽管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两只手,却像历经严寒烈日风吹雨打的树皮,粗糙坚硬,遒劲有力。而现在,父亲的左手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右手却软绵绵的,没有半点力气,我悔恨自己没有早点回家,没有把父亲早点送到医院。前几年,一到腊月,父亲总是要到医院住个十天半月,挂挂水,扩张一下血管,调养调养,再回家过年。这一年,因为妈妈身体也不好,到外地医院检查了几天,本来需要住院治疗的,考虑到父亲没人照顾,开了点药回家吃,准备过了年再说。说也奇怪,妈妈身体不好那段时间,父亲倒是比以往好了许多。就这样,住院调养的事就给拖了下来。谁知这次侥幸和大意,竟铸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
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被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当晚转到重症监护室,我颤抖着手,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间已是农历二十五凌晨。我问医生“您看我父亲还能有多少时间?”“很难说。”“能过得了年吗?”“恐怕过不了。”当时离过年只剩下四天时间,如果年都过不了,说明父亲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我和妈妈商量,既然这样,那就按照父亲的要求,让他回老家,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吧。
在“老家”家屋的三个月
随着弟兄姊妹陆续进城谋生,家里的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四面漏风。腊月时节,天寒地冻,没有空调肯定不行。于是,我连夜安排:一拨人赶紧回家打扫房子;一拨人回家把二姐家的柜式空调机拆下,买新的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拨人天一亮就到市场敲门,买棉被、塑料纸等用来将门窗裹住,防止透风。就这样,大家饭都没顾上吃,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把老家的房子整理得可以住人。妈妈催着把父亲送回家,我不死心,找到院长,问到底能不能熬到过年。经过紧急会诊,院长以肯定的口吻和我说:“现在情况还可以,必要时,把呼吸机用上,确保老英雄过年。”我如释重负,长长出了口气,全家人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
那一年的年夜饭,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没有父亲参加的年夜饭,大家虽然围坐在一起,心却都飞到了病房。我们草草吃了点饭,留下几个人照顾妈妈,其他人都来到了医院。按照规定,重症监护室只有下午3点到5点可以探视,其他时间不让家人进去。我要其他兄弟姊妹以及孩子们在观察室里等候,我自己则在观察室门前不停张望,来回徘徊,默默祈祷。直到午夜的钟声敲响,绚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密集的鞭炮声响成一片,我双手合十:“大,您迎来了新年!”
一天、两天、三天……父亲奇迹般的过了正月初五,医生告诉我,需要把父亲的气管切开,不然吸痰器已经很难把胸部的痰吸出来。吸痰的过程相当痛苦,要把管子插到很深的地方,每次吸痰父亲都疼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脸上的肌肉不停的抖动。切开气管,吸痰就容易多了,但同时意味着父亲即使大脑意识恢复,也不可能再讲话了。不切气管,痰吸不出,意味着就要活活被堵死,切开气管,可能多活些时间,但从此剥夺了父亲讲话的可能。切,还是不切,真是万分纠结,万分痛苦。最终,还是让父亲多活一天是一天的念头占了上风,同意对父亲进行切管手术。
父亲好强了一辈子,在家说一不二了一辈子,最终却在自己的生死问题上,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恐怕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由于这个决定,父亲创造了他生命的奇迹,同时也饱尝了无尽的痛苦。当初的决定,对还是错,我至今仍然无法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还有这样一次选择,我一定不会同意让父亲再受那么多苦的,因为,父亲这辈子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战争年代六次负伤,父亲前前后后做过五次大的手术,前面三刀后面两刀。每次都从鬼门关前闯了过来。医生说,要是再有需要,连下刀的地方都没有了。
父亲的生命 纠结的兄弟姐妹
切开气管,理论上就要呆在重症监护室,因为那里空气是经过消毒的,实行的是无菌操作。而普通病房,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切开的气管直接和空气接触,极易引发感染。又过了大概有十天时间,妈妈和二姐坚决要求将父亲接到普通病房。她们的理由是,切开气管,是为了让父亲多活几天,让家里人多陪他几天。像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重症监护室,不让家里人陪伴,连什么时候走了都不知道,那切开气管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在征得其他家庭成员同意后,把父亲接了出来。医院对父亲很照顾,特意给安排了一个单独病房,便于家人陪护。此时,虽然父亲的头脑仍然没有恢复多少,但眼睛已经可以睁开,对声音也有反应,喊他时,有时眼睛会朝你看。神奇的是,尽管经常发烧,但只要用点退烧药,马上就好了。就这样,父亲在医院里过了三个多月。
农历四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刚从医院看过父亲,还没到家,就接到电话,叫我赶快回去。等我跑到医院,病房里已经挤满了人,只见父亲面色发紫,浑身发抖,大口大口地喘气。院长闻讯也赶了过来,经与在场的医生商量后,和我说:“赶紧回去吧,今夜可能危险!”我一听这话,让弟弟赶紧回二姐家拿父亲的衣服,父亲的送老衣早就准备好了,从里到外都是部队的老式军装,因为父亲身材比较高大,为了找齐这套衣服,费了不少功夫。我自己则和二姐坐上医院的救护车把父亲往老家送。好在老家的房子此前已经收拾好了,否则还不知乱成什么样子。一路上,我抱着父亲,不停的呼喊:“大大,挺住,挺住啊,大大,坚持啊,坚持啊,大大,马上到家了,马上到家了。”二姐边喊边哭,嗓子都哑了,我们也都忍不住地流泪。十几里的路程,要在平时,开着车子,眨眼就到了。那天却觉得十分漫长,最大的担心是父亲在路上就走了,那他这些天的罪就白受了。一直到进入老房子里,七手八脚地把父亲的衣服穿好,瞧瞧父亲还在喘气,大家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医院对父亲十分尊重,特意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到我家,并带来了氧气瓶,希望能让父亲尽可能多在家过一点时间。
父亲回家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早到晚,前来探望的父老乡亲一波又一波。来看他的很多是老年人,不少人随意在房间里抽烟吐痰。按说,对于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说也奇怪,父亲像是百毒不侵,竟然没有丝毫影响。只要有人来看,父亲就静静的,眼睛望着,像是能听懂人家的话。到了晚上10点以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张大着嘴喘,脸憋得通红,吸氧也没有用。为了能够让我陪伴父亲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单位主要领导对我很照顾,要我请假在家。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听说父亲快不行了,赶来看望后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和你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们都希望老英雄长命百岁,但依目前的情况,与其让老人家这样受罪,不如停止一切治疗和进食,让老人家早点走。我想,老英雄如果自己能够决定,他一定会同意的。”我深知,像这样非同小可的话,不是铁杆兄弟,是不会说的。而且,他的说法是理智的,是为了父亲好。但对我来说,父亲多活一天,毕竟多了一天双亲同在的时光,而一旦父亲撒手人寰,则永远也无法再见。我紧紧握住朋友的手,内心万分纠结,百转千回。第二天,我把朋友的建议和妈妈讲了,妈妈说:“他活着也真是太受罪了,我也有这个想法,你们兄弟姊妹们商量一下吧。”
我兄弟姊妹共七个人,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最小的弟弟强烈反对,说父亲眼睁多大的,我们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二姐多年来一直服侍父亲,是尽孝最多的一个。一天24小时,二姐和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亲戚三班倒的看护父亲。妈妈年龄大了,二姐总让她多休息会儿。那位亲戚对生命监护仪、吸痰器、氧气瓶等一些设施不会使用,这样,看护主要任务就落在二姐身上。二姐对父亲的了解最多,深知父亲的苦楚,同意放弃治疗。大家意见不一,最后小弟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就你说了算吧。”“我要一个人静静地想一下……”说着,我独自离开了家。

让父亲的生命融入春天
家里现在的房子,并不是我小时候住的草房,而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建的六间瓦房。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件家什、每一件农具,都留下父亲的气息,承载着父亲太多的辛苦、太多的依恋。对那些街坊邻居,父亲更是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也许,这正是父亲坚持要从家里走的原因吧。
四月的乡村,麦浪滚滚,满目苍翠,一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小花在河边竞相开放。方瓜吐着金黄的花蕊迎风摇曳。父亲5岁时,奶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不久,爷爷也离开了人间,留下一个姑姑和父亲相依为命。早些年,姑姑健在时,我曾问过她,父亲的生日是哪一天,姑姑告诉我,她也忘了准确的时间,只记得是方瓜开花的季节。方瓜开花的季节,不正是当下吗?我的心猛的一颤。父亲生在四月,走在四月,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就让他的生命融入春天,融入自然,万古长青吧。主意既定,我在最后征得妈妈的同意后,决定请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回去,同时带走一切药品和医疗器械,只给父亲喝水,不再通过鼻饲进食。医生护士刚走,全家人已哭成一团。我爱人不停地劝我,她自己也不禁泣不成声。因为,我们知道,就在这一两天时间里,我们将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到了晚上,二姐照例给父亲擦洗身体,发现父亲又发烧了,身上热得烫人。要是在医院,或是医生走之前,给颗退烧药吃,或许很快又好了。可现在,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响,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似乎在说,实在受不了啦,让我早点走吧,似乎又在说,你们一个个不闻不问,怎么这样不孝。“去医院拿点药吧?”弟弟首先动摇了。父亲的呼吸声像是针一样戳在我的心上,我跪在床前,双手抚摸着父亲的面颊,眼泪不停地往下掉,父亲则紧紧攥住我的手。二姐叹了口气,从兜里拿了颗药出来。原来,她在医生走前,悄悄的把药藏了几颗。大家这才知道,二姐虽然同意放弃治疗,其实她比我们更舍不得父亲,只是更不忍心看着父亲受这么多罪!说也奇怪,父亲吃了药以后,不但烧退了,不喘了,眼睛好像也有神了。连续四天,父亲就靠喝点水维持,精神居然出奇的好,一点没有要走的样子。我把情况打电话告诉了院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估计是不行了。这样吧,我让医生过去采点血化验一下,看电解质紊乱没有?如果电解质没有问题,干脆再回来住院!”
让我们大喜过望的是,父亲的血液化验结果竟和在医院时一样。看来父亲不愧是英雄,果真非同凡人!就这样,父亲再次回到了医院。
淬过火的钢刀 真正的伉俪情深
201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0年。为了纪念这场伟大战争,凤凰卫视在全国宣传十名战斗英雄,包括牺牲的黄继光、杨根思,还有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的原型杨育才等,杨育才早几年也已经去世了,活着的据说连我父亲在内,只有三个人。由于父亲已经不能讲话,摄制组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主要采访了父亲的老战友、原沭阳人武部宋吉月政委,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老营长、无锡市民政局原优抚科长栾波同志,以及父亲同连队战友、浙江金华离休干部王向阳同志。后面这两位同志,都是在媒体宣传父亲的事迹后联系上的。当摄制组最后来到病房拍摄时,我告诉父亲:“这个片子是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拍的,将在凤凰卫视《大视野》节目播出,全世界都能看到。还有,宋伯伯、栾伯伯、王叔叔都很关心你。”父亲像是听懂了我的话,嘴动了动,一滴泪水悄悄地从眼角流下。这时,我才肯定,父亲是有意识的,至少这个时候是有意识的。由此我想到,当我们决定放弃治疗时,父亲其实是知道的。一方面他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也想早点解脱,另一方面,他又舍不得与他朝夕相伴近50年的妈妈,舍不得我们这一群孩子。也许,潜意识里,他更想等来他入朝60年的日子。最终,父亲体内旺盛的生命力在和病魔搏斗中占了上风,就像一个坚守阵地的战士,不到最后一刻,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正如一个诗人所说,父亲不愧是淬过火的钢刀!
专题片拍好后,我们天天盼着早点播出,盼着能让父亲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谁知,由于复杂的原因,据说也有出于对美关系的考量,要选择一个最佳时机,整个播出计划被一推再推。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近200斤的体重,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就像一具睁着眼睛的骷髅。我和二姐说:“看来我大是等不到这个片子播出了。”妈妈则紧紧地攥住父亲的手:“老头子,你一定要坚持啊!”妈妈的身体原来很不好,但自从父亲病重以后,妈妈成天和二姐服侍父亲,自己反而好了起来。父亲天天都要打吊针,因为他自身大多数时间没有意识,手会不停的动,一动容易鼓针,水就不滴了,需要重打。这样,父亲又要多受一遍罪。为了避免,在父亲吊水时,妈妈就一直把父亲的手握着,除了上洗手间的短暂时间之外,绝不要我们替。我们感到,虽然父亲不能讲话,甚至没有意识,但只要攥着他的手,妈妈就觉得踏实。什么是伉俪情深,父母之间这种无言的爱,才是真正的伉俪情深。
宣传英雄的电视片播出了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多,大约在2010年11月,父亲又一次病危,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连夜把父亲送回家。到家以后,时间不长,父亲有如神助,又一次挺了过来。妈妈说:“你大看样子离不开家,离不开老邻居们,这次回来,再也不回医院了。”我们也都认同妈妈的说法,觉得老宅是块宝地,似乎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着父亲。星期天、节假日,只要不是工作实在脱不开身,我都尽量回老家陪伴父亲。
父亲躺在家里,每天通过鼻饲打三遍营养液,什么水也不挂,什么药也不吃。除了不能说话和日渐消瘦外,情况比在医院还要好。在医院的时候,用于鼻饲的那根管子,至少一个月换一次,可到家后,一直到去世,几乎一年时间,一次都没有换过,居然一点事没有。医生们听说,都感到不可思议,直呼父亲为老神仙。
为了防止父亲躺得难受,家人每隔半小时为父亲翻一遍身,翻身时,一个人小心地抱着父亲的头,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双手使劲把父亲托起,调整方向后轻轻放下。过一会儿,再把父亲扶起来,让他整个靠在身上。
那段时间,我夜里最怕的是听到电话铃声,害怕传来父亲的噩耗。由于我干的是公安工作,偏偏电话特别多。特别是刚刚睡着的时候,电话一响,就像被电触一样,砰的一下坐起来。虽然看到显示的号码后,心放下了,但再想入睡,可就难了。
我想,父亲看样子是一定要等到凤凰卫视节目播出了。如果是这样,真希望节目能迟些播出,越迟越好,这样父亲就能多活一些时候了。同时,我又希望节目早点播出,父亲活的真是太苦了,太不容易了。为了父亲的存在,为了家的完整,让父亲受这么大的罪,是不是太残忍了?就这样,在纠结中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 在这一年的年底,节目播出。我请电视台的同志,把它和央视及省、市电视台以前播出的片子录在一起,制成光盘,回家以后,一遍一遍在父亲床头放。尽管父亲不能说话,也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似乎在静静地听,静静地想,似乎又回到了他金戈铁马的年代。
几回过年 几度光景 耐寻思
转眼到了腊月,想到几年前,过春节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叫做《过年》的文章,回去读给父亲听。那时的父亲虽然不能下地行走,但思维仍然清楚,听了我的文章,夸我写得不错。才不过几年时间,就不知父亲今年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过了。我们商定,只要父亲在,今年的春节,兄弟姊妹七个以及孙辈们,全家老小二十几口人都在老家过年,一个也不能少。
为了确保父亲过得了春节,我们从医院开来脉络宁等扩张血管的药,连着给父亲挂了十几天水,好在二姐轻车熟路,不用请护士,独自包办。那年的年三十,家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我们早早的在院子里支了两口大锅,天不亮,就开始忙碌起来。洗菜的,劈柴的,烧火的,做饭的,炒菜的,满院子都是人。我则拿过久违的毛笔,写了一副对联:“:欢天喜地庆父寿,合家团圆过大年”。虽然谈不上对仗工整,但确确实实表达了当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吃饭前,我们像小时候一样,轮流着给父亲磕头,妈妈则代表父亲,一个一个给我们压岁钱。我们都知道,这是父亲在世时,一家人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所以第一杯酒端着走到父亲面前,不管能喝不能喝的,全部一饮而尽。父亲始终望着我们,眼睛再没有了从前的威严和犀利,而是流淌着无尽的疼爱、不舍和眷念,让人看了人心碎。
饭后,大家一齐出去放烟花。我小弟做点小生意,平时比较抠门,一个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这次过年却慷慨地买了很多烟花。随着 “嘭” “嘭” “嘭”的巨响,烟花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绽开五颜六色,有的像流星徘徊在夜空,有的像万寿菊欣然怒放,还有的像仙女散花……一朵朵礼花从天而降,姹紫嫣红,把夜空装点得美丽婀娜,把大地照射得如同白昼,真是璀璨夺目,火树银花。我想,父亲的生命虽然绚丽多彩,可在茫茫宇宙中,不正像这美丽的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吗?今天,大家在一起放烟花为父亲庆祝,明年的今天,父亲再也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在那边会寂寞吗?
回到房间,我们把电视打开,一边欣赏着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唠着家常,唠着唠着,唠到了从前的时光。二姐说:“弟弟,你还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情形吗?”这一问,重又勾起了我遥远的记忆。
那是物质、文化双重匮乏的年代,过年,是孩子们最大的向往。能放开肚皮吃几天的白面馒头,能穿上新衣服和大人一起走亲访友,能贴春联、放鞭炮、看大戏,还可以怀揣大人给的几毛压岁钱到城里逛一逛,有什么比这更解馋的呢?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巴巴的盼着过年,记得不大清了,大约总在过冬以后吧。冬大如年,过冬,就像是过年的预演或者彩排,只不过氛围没有那样浓,时间没有那样长,也少有过年那样热闹罢了。过了冬,就一天一天地数着到年的日子。时间老人似乎有意打磨孩子们的耐心,你急他不急,仍是慢腾腾地向前挪。好不容易到了腊月,时间好像突然加快了脚步,腊八一过,祭灶就不远了,祭灶一到,春节终于屈指可数了。那时学生放寒假是从祭灶前一天开始的,要准备期末考出好成绩,要争取把“三好生”的奖状捧回家,要打算寒假怎么痛痛快快地玩,心里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孩子们盼过年,最忙最累最操心的是父母,为了能让孩子们过年吃得好一点,玩得开心一点,还能穿上件新衣服,父母从年初就精打细算,盘算着年怎么过,年货怎么买。数九严冬,父亲摸黑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用独轮车推着几百斤的菜出去卖,为了能多换回几个钱,往往去很远的集市,来回要走近百里的路。过去不像现在,雨雪天很多,西北风呜呜的刮,天出奇的冷。父亲凌晨出去,到天黑还没有回来。外面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一家人急得不行。那时农村没有电,太阳一落山,村庄黑黢黢的,整个儿笼罩在无边的夜幕之中。母亲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一边念叨,一边张望,一边悄悄地抹眼泪。忽听外面一阵狗叫,妈妈说,可能回来了。我们姊妹几个赶紧迎上去,果然是父亲回来了!只见他,眉毛胡子都被雪冻住了,浑身上下就像雪人一样。多少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两句诗时,不禁唏嘘不已。
生命的奇迹 在后人心中延续
“妈妈,你猜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父亲变老了的?”没等妈妈说话,我自问自答道:“是从我大不让二弟打自己的孩子开始的。”一次,孩子不听话,二弟举起巴掌准备教训他一顿,父亲发现了,一把将孙子拉到身边,大声呵斥起我二弟来。像父亲这样经历过枪林弹雨,性如烈火的人,只有到了知道“隔代疼”时,才真的老了。我说,“还有一个故事呢!” “什么故事,说来听听。”妈妈饶有兴趣地问。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稍有错误,抬手就打。挨打,成了这个人的家常便饭。有一天,不知什么事把他父亲惹毛了,又被狠狠打了一拐棍。这人被打后嚎啕大哭。这时,他父亲骂道:“没出息的东西,我从前打你,从来不像这样,这次怎么哭鼻子了。”这人说:“从前挨打,感到很痛,说明父亲身体有力。这次挨打,一点不疼,看来父亲老了,没有力气了。儿子是心里疼,所以哭了。”
忽然,我发现父亲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嘴唇不停地在动。我趴在父亲耳边:“大,您听到我们在说什么了吗?”
春节七天长假很快过去了,除了妈妈、二姐和一位亲戚留在父亲身边,我们都上班去了。到了双休日,大家又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老家,来到父亲身边,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妈妈告诉我们,家里人少的时候,父亲眼睛很少睁开,一点精神都没有,只要院子里人多起来,他的眼睛就睁得老大,还能顺着声音看,像是什么都知道。就这样,送走了春天,告别了夏天,父亲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季节。国庆长假,家里所有的人都在陪伴父亲。2011年10月3日,父亲在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后,终于油尽灯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
父亲在战场上创造了奇迹,在和病魔搏斗中同样创造了奇迹。一位白发苍苍的专家告诉我,气管切开后,能在尘土飞扬的农村,活过近两年的时间,在他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经历中,从未听说过。父亲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父亲?
父亲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数不清的花篮、挽幛、唁电,寄托着人们对父亲的怀念和崇敬。
1995年采访团成员,新华社驻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陈辉同志赋诗一首:
鸟枪射雕一世功
伤痕累累百战雄
隐姓埋名居乡里
默默无闻甘为农
枪林弹雨不畏死
战天斗地敢脱穷
壮士不言留美名
一代英雄百代荣
原昆明市委书记,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同志送来挽联:
攻济南战淮海渡长江枪落美机赫赫声名扬天下
奉乡梓行善事布仁德功高不居煌煌风范励后人
我也含泪写下:
眼中含泪紧攥孩手依依不忍别离去
心底泣血轻抚父面悠悠悲恸恨糜涯
“大”,您选择在节日的时候离开,是便于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聚在一起吧?您放心,我们已经和妈妈讲好了,明年把老家的房子翻盖一下,每年的10月3日,我们都会一起来到这里,来到您辛勤养育我们的地方,为您磕头,给您上香。
“大”,您听到了吗?
你是一位老兵,
曾在战场屡立战功;
你是一位老兵,
惜别军营隐功埋名。
春风年年,春风年年把你寻找,
日月天天,日月天天把你询问,
你在哪里,我们的功臣,
祖国时刻牵挂在心。
你是一位老兵,
曾以生命保卫和平;
你是一位老兵,
挥洒青春,造福乡亲。
鲜花朵朵,鲜花朵朵为你盛开,
硕果累累,硕果累累为你作证,
你在哪里,我们的英雄,
一片热土,几多深情。
你是一位老兵,
曾用热血书写光荣,
你是一位老兵,
至今仍然不愿出名,
战旗飘飘,战旗飘飘为你礼赞,
兵歌声声,兵歌声声为你称颂,
你在哪里,我们的老兵,
三军将士向你致敬,
三军将士向你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