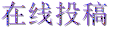皖南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是新四军皖南部队里一个26 岁的女战士;2015 年我100 岁,有幸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章”。
高唱着《别了,皖南》歌曲踏上北移征程
我记得在新四军转移前夕,驻地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到处造谣,说新四军此行是开到东北去,甚至说到苏联去的,以动摇皖南新四军官兵的军心。
转移前,新四军军部曾在云岭吴氏大宗祠内举行告别皖南民众大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表“告皖南同胞书”的演讲,其情景热烈而悲壮。1941 年1 月4日,新四军离开皖南驻地的那一天,新四军军部主办的《抗敌报》出版了“告别号”,在“告别号”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临别之言》,还发表了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领导同志联袂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与驻守三年的皖南告别。遵照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皖南部队6 个团9000 余人编为3 个纵队,高唱着《别了,皖南》的新四军歌曲,告别云岭,告别皖南,踏上征程,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词、新四军作曲家任光谱曲,成为此次皖南新四军战略大转移的序曲。《别了,皖南》的歌词如下:“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到达目标!”铿锵有韵,军味浓郁,鼓舞士气,气壮山河。
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40 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即将离开驻守三年的皖南泾县云岭,北上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有一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作曲家任光送来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词《别了,三年的皖南》,请任光谱曲。袁国平对任光说:“新四军在皖南已整整三年了,同志们对皖南都很有感情,现在即将北渡长江,得给同志们打打气,以振作精神,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听了这番话,任光很受感动,接过歌词便全力投入创作。任光的妻子徐韧也在一旁出了不少的主意。一天上午,叶挺军长路过任光住地,听到任光一边哼唱一边修改,也提了一些意见。3 天后,歌曲《别了,皖南》终于完成并被传唱。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这首歌曲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主要原因是,她充分表达出了我们江南新四军将士当时那种对皖南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她不啻就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别了,皖南》是我们最喜爱、最敬仰的新四军作曲家任光的人生绝唱,是他留给皖南、留给新四军乃至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歌曲。因为当年新四军9000 人马唱着《别了,皖南》告别云岭时,作曲家任光、徐韧夫妇也随军部直属队踏上撤出云岭的征途。部队遭国民党军伏击时,任光和军部直属队的许多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被国民党军发现,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向人群射击,任光不幸中弹牺牲。
任光的妻子徐韧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她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难友,我们一起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女生队里。才智兼备的徐韧与残暴的敌人斗智斗勇,她甚至利用敌人组织集会之机,登台清唱了两首歌,直到女囚们鼓掌击拍喜气洋洋,宪兵才惊觉上当,原来徐韧竟是用英文演唱《新四军军歌》和《别了,皖南》。
我被编在第三纵队冒雨出发
1915 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从小到上海随父就读,在上海长大成人。1939 年11 月初,我离沪赴皖,参加新四军,那年我刚满24 岁。
原先,我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光荣牺牲的噩耗之后,我便征得党小组长李淑英的同意而毅然离沪赴皖从军,为妹妹报仇,为抗日献身。到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亲自接见了我这位“抗日烈士冯玲的亲姐姐”的新战士,并使我以百倍的热情,立即投身到紧张而又繁忙的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的学习、训练中去。很快,我就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我们三支队的司令员是张云逸(兼),副司令员是谭震林。
虽然我们分散到乡村去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但是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乡绅和广大民众打交道,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新四军身份,积极工作,并定期回团部汇报、请示。两个月后,我们6 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五团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沈锐是组长。五团的团长是徐金树,政委是林开凤。在皖南事变之前,我一直都在三支队五团的民运小组里从事着民运工作。
按照云岭新四军军部大转移北上抗日的部署,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优先分批转移、渡江北上的。而且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协商结果,新四军的3000 多名非战斗人员,已经从1940 年11 月开始,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并且全部到达了江北根据地。
但是,由于一向好强的组长沈锐,坚持“要走就堂堂正正地走,而不要悄悄地走”,使得我们错失了机会,只得随同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是张正坤,政委是胡荣),于1 月3 日傍晚从繁昌冒雨出发,随着大部队转移北撤。我们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由五团所在的三支队和军特务团合编组成,约2000 多人。我们五团跟随军部前进,为全军的后卫部队,任务是保卫军部,由叶挺直接指挥。
这山间泥泞小路上“一夜最少要走20 里山路”的夜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长大,来新四军只有一年多时间,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湿,显得更加沉重,因此好几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沟里去,战友们把我拉上道路继续行军,湿透了的衣裤被风一吹寒冷透骨。
跟随部队在丕岭上突围行军
1 月6 日,我军行至丕岭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7 个师8 万兵力包围袭击。我所在的第三纵队五团,1 月6 日上午7 时许,在丕岭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二○团搜索部队的袭击。丕岭战斗,也便成为了皖南事变中的第一战。
丕岭是皖南泾县茂林镇与榔桥镇交界的一座上七下八里的大山,四面群山环绕,其中以丕岭为主峰,海拔908米。丕岭多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地势十分险要,山间有一条狭窄的小道盘旋而上,是茂林古时通往旌德的必经之路。古道边,一条山涧顺山而上,清澈见底。从坑口村到丕岭到榔桥镇,爬山要8个小时。丕岭战斗中,我新四军部队兵分两路向丕岭进攻:一路从正面沿着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侧面绕到敌人阵地背面,形成前后夹攻之态势。经过20 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就把顽军打得晕头转向,向着百户坑方向狼狈逃窜,丕岭阵地完全被我军占领。丕岭之战,共击溃敌人一个连,歼灭了其中的一个排,缴获了3 挺轻机枪。
霎时,前方不断有伤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得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去抢运伤员,还得配合卫生员的包扎救护工作。尤其困难的是安置重伤员就地隐蔽养伤的工作,我们是以极大的爱心,强忍着泪水在努力地做着。有一个重伤员哭着对我说:“同志,你们要走了,就不带我们一起走?”说得我眼泪夺眶而出,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帮他擦去泪水,耐心地劝慰他以大局为重,听从命令安心养伤,要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的。

分散突围误入敌阵
1 月12 日夜间,我跟随部队在位于茂林东南方的丕岭一带突围行军。我们五团与军部、教导总队等一块共计400 多兵力,从石井坑东南,翻越最高峰——火云尖,突围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遭到国民党军第一○八师的堵击,多次冲杀,终因兵力悬殊,未能突出重围。此时,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叶挺军长即于当晚在大园村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命令部队以石井坑为中心,分头撤退,分散突围”的决定。
因为我们是在激战七天七夜之后的夜间突围行军,体力消耗非常的大,好多人都出现了严重的体力不支。再加之连日战事频繁,人已疲惫不堪,虽然四周枪声不断,我们仍困倦得常常在行走中不时睡着。有个叫周韶华的女战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弹牺牲的。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3 个女战士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
1 月13 日拂晓时分,饥渴困顿,促使我们3 个女战士穿破荆棘去寻找水源。当我们终于在山腰间找到水沟,喝着冷水的时候,只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听得喜出望外,以为我们的部队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去。
不料这是顽一○八师驻地,我们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就被安置在火堆旁坐下烤衣服,这时才发现我新四军军部敌工部的林植夫部长已经坐在那儿了。当他认出我们后,只是无奈地推推眼镜架,痛苦地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后来我才知道,林植夫部长是12 日夜间行军时与叶挺军长失散之后,遇到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队,13 日被推为谈判代表,随同一○八师派来的那个排长一道走出山口去谈判,结果一到一○八师师部即被扣住,关押到这儿来了。
我们为自己的受骗下山而痛悔不已。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和我的新四军女兵战友们一块,开始了长达4 年多的女囚生活,这一天是1941 年1 月13 日的凌晨。
两天后,我们被押解到徽州歙县的“定潭集中营”关押。后来我才知道,皖南事变中我军的损失太惨重了,几乎是全军覆没:除了2000 余人分散突围、包括叶挺军长在内的许多新四军将士被俘、失散外,其余壮烈牺牲。
随后,我们又从安徽的“定潭集中营”经浙江被转移到江西的上饶八都,最后于1941 年3 月底抵达周田村的“上饶集中营”。我们女生队30 人,被捕前都是分别在新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印刷厂等单位,担任政治、文化教员和机要、民运等工作的,被编在军官大队五中队三分队(女生分队),监禁地点在下周田村。就在这集中营关押的特殊环境里,我们女生队的新四军战士,在已经悄悄成立的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面对顽军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措施,轮番对我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残酷折磨,与顽军进行着殊死的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8 月29 日至10 月10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于10 月10 日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负责关押囚禁皖南事变战俘的国民党东南分团才被迫无条件解散,我们这些已经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了近5 年的新四军将士们,才逃脱了牢笼、获得了自由,开始了北上寻找组织的艰难旅程。
云岭军部的青春之歌可以作证,皖南事变的丕岭硝烟可以作证,“上饶集中营”的阴森牢底可以作证,今日云岭的战地黄花可以作证,我们,不愧为“铁的新四军”!
(江志伟整理,汪苹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