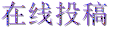父亲潘孔池离开人世时很安详,熟睡般的面容,显得那么平淡、普通。父亲生前常念叨:在那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无数的战友、领导牺牲了,而我却幸存了下来,组建家庭,生儿育女,衣食无忧,晚年幸福。“这一生,我知足了。”
小和尚参加了新四军
1925年12月的一天,父亲降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一个小山村里。
父亲童年时,家境贫穷。他七岁时就帮富人家放牛,十岁时,其祖父、父亲相继病逝。为了还债、活命,父亲被家人以六块银元的价格卖到当地庙里做了小和尚。那时候和尚的社会地位很低,幼小的父亲念经,学做法事,更多的时间是去化缘,干农活(寺庙有少量土地)。父亲的不幸遭遇得到附近一名叫刘鳯竹道士的同情,他时常对父亲嘘寒问暖、送衣送食,讲做人做事、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还叫父亲利用外出化缘、做法事的机会帮他收集、传递情报,给外地人(新四军)带路。后来父亲才知道刘道士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利用道士这一特殊身份从事地下抗日活动。1944年2月的一天深夜,刘道士匆忙叫来父亲和当地两名青年,拿出一张写有地址和人名的纸条给父亲,告之,他们和父亲的抗日活动被日本人发现了,叫他们连夜逃走。
按照刘道士的指引,第二天上午,父亲他们找到了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沿江团。因为有刘道士的纸条,加之父亲为沿江团好几个人带过路,所以没有任何障碍父亲就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沿江团二营六连三排八班的一名战士。
后来父亲才知道,在他走后的第二天一早,日军便包围了刘道士的道观。没有找到任何人,便一把火烧了道观。以后,父亲曾多方打听刘道士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托人查找,但始终未有结果。
前不久,我查找有关资料,得知一条线索:在父亲参加新四军的第二个月(1944年3月),沿江团花山游击队曾从国民党顽军手中营救下一位新四军地下工作者——常道士。这个姓常的道士和刘鳯竹是同一人,还是一起的,我也无从考证,但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国难当头之时,许多出家人也没有置之度外,而是参加抗日,舍生取义,杀敌报国。
父亲刚参加新四军时,配发的是一支七师自造只能打单发的匣子枪,连队只有一挺机枪,有的连还没有机枪。战士们的武器都是缴获来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子弹也不多,老战士还有个十发八发的,新战士只有两三发。为壮军威,战士们把树棍、高粱秆塞进子弹带里,鼓鼓囊囊,挂在身上好不威风!班长刘和根带父亲砍来一根粗细适中、两米多长的毛竹,教父亲用麻绳、布条把刺刀牢牢绑在一端,说跟小日本拼刺刀用。在随后的几次战斗中,父亲同其他新战士一样,手握这一特殊武器,冲向日军。“还管用”,父亲告诉我们,新四军战士没有经过几天正规训练,跟日本人拼刺刀,单个较量、近距离较量我们肯定是吃亏的,于是就四五个战士围住一个日本兵,远远地抵住他,三八大盖再长也长不过我们手中的家伙,乘他稍不注意,一刺刀就干掉他了。父亲不无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打淮海,我们的武器就不一样了,卡宾枪,子弹尽管打,要是那时(指抗战)有就好了,不仅能多杀鬼子,而且我们许多人也不会牺牲了。”
父亲由于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再加上岁数较小(还未满20岁),被抽调到沿江团警卫排担任副团长周亚农的警卫员,开始了他新的抗日征程。
新中国建立初年,已是一名解放军基层指导员的父亲,身着崭新的军装,腰插一支勃朗宁小手枪,肩挎一支驳壳枪,回到老家探亲。小山村的男女老少争先恐后过来围观、问候,但不久,父亲从乡亲们言谈举止和眼神中看到了隐隐约约的迷茫、痛楚。当地村干部告诉父亲,打日本鬼子时,小山村先后有28人参加新四军或新四军游击队,全国解放两年多了,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人,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沉默了,没几天就悄悄地离开了家乡。之后他转业江苏,结婚安下家,把老母亲(我奶奶)接来养老送终,几乎就没有再回家乡去过。等再回去的时候已是1996年初,他已身患绝症。父亲坚持在去世之前,要把子女带回老家看看,认认家乡的面貌。此时,我终于大悟:许多老将军解放后很少回家乡,也是担心烈士遗属“见友思亲”、引发悲情的缘故吧。
解放军基层指挥员
战火催春,在部队里,父亲很快从一名警卫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他先后担任过团炮兵连司务长、团管理员、代理连长、政治指导员。
晚年父亲病重期间,曾经给我讲起最令他难忘的一次战斗。
1948年3月初,解放军山东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发起了周(村)张(店)战役,在取得胜利后,又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发起了昌潍战役。战斗打响后,父亲所在的七纵部署在胶济线中段益都地区(现青州),经八天浴血奋战,成功阻击了济南国民党军队增援,确保了昌潍战役的胜利。
父亲时任华野七纵二十师二二一团管理员。一天傍晚,一位满脸是血、满身是灰的战士急奔而来报告:前线一个阵地失守了,一个连打光了。那个失守的阵地位于一条大路旁的山包上,位置十分重要。团里预备队早已用光,情急之下团长命令我父亲带领警卫排把阵地夺回来,牢牢地守住,不放敌人一兵一卒进来。
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月色很亮,阴风阵阵。经过数小时来回穿插,父亲一行悄悄地摸上阵地。“怪了,怎么一个敌人都没有?”稍加搜索,这才发现占领阵地的40多名国民党军龟缩在阵地山背后的一处凹陷处烤火睡觉呢。父亲他们先是悄悄接近,然后一拥而上,“缴枪不杀”的喊声划破寂静夜空,这批国民党军士兵乖乖当了俘虏。
夺回了阵地,本应高兴,可父亲却犯愁了,这批俘虏该怎么办?按规定,战场上抓到俘虏,要派人押回后方,交由专门部队和人员看管。可父亲身边只有20多人,夜间押送,四周敌我交织在一起,人派少了不安全,人派多了,阵地怎么办?父亲赶紧和几个老班长商量,急中生智,决定干脆分头做单个俘虏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在战场上加入解放军。没想到,这批俘虏大都出身穷苦,多是被抓的壮丁,他们一个个表态愿意加入人民解放军,一起守阵地。
天刚蒙蒙亮,大批国民党援兵正欲通过父亲他们阵地旁的大路时,遭到一顿痛击,敌人退下了。“怎么搞的,这阵地不是说昨天傍晚就攻下来了,怎么一个晚上未闻枪声,又被解放军占领了?”回过神来的国民党援兵恼羞成怒,摆开架势准备进攻。“撤!”在父亲指挥下,阵地只留下两名老兵,其余人员撤到山背后的凹陷处。“轰轰轰”一阵炮击后,父亲他们又很快进入阵地战壕,20多支卡宾枪加其他武器同时开火,援兵又被打退了回去……一天下来,这边阵地牢牢地守住了,那边潍县城被山东兵团九纵攻陷,接着济南国民党援军只好撤退了。
团长上阵地见到我父亲,连声说:“好,好,好,你就留下当连长吧。”待父亲正式看到任命时,却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团政委说父亲不但会打仗,还会做政治工作。这一仗下来,父亲荣立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随部队进入皖南剿匪,在一场战斗中头部中弹。父亲在贵池军分区医院病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月,被救活下来。“没有被日本鬼子、国民党正规军打着,差点让土匪打死”,父亲挺懊恼的,这次受伤也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朝鲜战争爆发了,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抗美援朝。父亲的伤痊愈后,部队已开赴外地整编,准备入朝。组织决定父亲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报到。
父亲的老部队老领导
父亲对老部队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因为新四军沿江团是他脱离苦海、明辨是非、成长成熟的地方。
1956年,父亲利用出差河北的机会,专程回了趟老部队。老部队给予了较为隆重热情的接待。父亲过去的通信员已是一名上尉连长,与父亲形影不离,伴随左右。那几天父亲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对老部队的热情接待十分感谢,对部队在朝鲜战场打赢多次恶仗、立下新功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老部队许多熟悉的领导、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心情轻松不起来。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很少回家乡,是怕那些烈士遗属们伤心;父亲很少回老部队,是怕自己伤心。他要把对老部队最深的印象、最美好的事情、最熟悉的战友定格在自己记忆里。
抗战时期,担任过父亲领导的有很多人,其中给我们子女印象最深的有两位。
一位是新四军沿江团的副团长周亚农。周亚农,湖北省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组建新四军时,被抽调过来担任营级干部。1944年2月,父亲参加新四军沿江团时,周亚农担任副团长。后来父亲被调到团部担任周亚农的警卫员。在随后较长的日子里,父亲和周副团长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俩形影不离,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官兵之情、兄弟之谊。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非同寻常。
1949年大军渡江前,时任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副师长的周亚农到江边检查部队渡江准备工作。当他听说邻近部队是七十四师二二一团时,就策马过来看望,在众多的老部下中他看见了我父亲,便飞身下马,紧紧和我父亲拥抱,问长问短。临分别时,他从腰间拔出一支小手枪送给我父亲。我父亲也不客气,“还有枪套呢”?周副师长哈哈大笑,又解下腰带,抽出枪套递给我父亲,还招呼我父亲的领导说:“跟你们师长说,这枪是我送的,他是我过去的警卫员,不准没收喽!”
未曾料到,周副师长长江边与我父亲一别,竟是永别。打过长江后,周亚农率部攻入浙江省境内时牺牲了。周亚农副师长送的勃朗宁小手枪,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于是就有了父亲挎两支短枪回老家探亲的故事。
第二位领导是傅绍甫,安徽省金寨县人,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父亲参加新四军时,傅绍甫是新四军沿江支队副支队长兼沿江团团长。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单位突然驶来三部吉普车。先是下来一名军人,专门打听我父亲。在找到父亲并被得到证实后,一位老军人在众多军人的陪伴下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和老军人相互凝视了一会,对方叫父亲姓名,父亲答“到”,这时,父亲也认出他了,赶忙叫他“傅司令”。父亲和傅副司令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紧接着傅副司令对父亲说了句让在场所有人吃惊的话:“逃兵!怎么离开部队的?”父亲一愣,然后简单把自己负重伤,老部队已开赴朝鲜一事作了汇报。傅副司令还是有点不满意:“你当时为什么不找我?你二十几年了也不来见我!”后来,他告诉我父亲,他还是最近从周亚农遗孀那里知道父亲下落的。傅绍甫时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当天晚上,父亲又应邀带上还是童年的我和妹妹,一起赶到部队招待所看望傅副司令员。
以后几年中,傅副司令员又几次约见过我父亲,每当谈到沿江团政委胡继亭、副团长周亚农牺牲时,傅副司令员总会难过得直流眼泪。
父亲常说:战友情胜亲情,人生最深战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