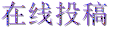蒋校长从小学退休回家的时候,我还是苏北农村的小学生,因为暑假到城里叔叔家玩,所以与蒋校长有了一面之缘。蒋校长的学校在本地农村,我之所以要强调农村,因为当时城乡差别极大。叔叔所住院子,住户多半是工人,辛苦的三班倒工人,即使这样,也比在农村做校长要好。
蒋校长推着二八大车进院子时,我正用调羹挖西瓜吃。看见蒋校长,我真正明白了作文里常写的慈祥与和蔼可亲是什么意思,蒋校长简直就是从作文里走出来的典型教师。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衣服虽旧,但他就有本事穿得挺阔。在经过我身边时,他弯下腰笑着问我“暑假过得开心不开心”。
第二天他带着外孙回乡下。外孙坐在自行车后面,我们挥手道别,都不敢说话,怕吵了上夜班的大人们的觉。
蒋校长一走,阿婆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说蒋校长是老革命,应该进城做校长的,却一辈子在乡下,把女儿的前途也耽误了。
后来老房子一片一片地拆迁,老家原址上立起少年宫,过去的街坊四邻分散去了城市各个小区,叔叔家也搬了,蒋校长也不知去向。
再见到蒋校长已是三十多年后。那次我受人之托,采访一位93 岁高龄的老校长。一般而言,事先我会收到被采访人先进事迹的材料。但这一次并无材料,对方告诉我老人姓蒋,是一位老革命,为人淡泊,1949年之前就是乡村教师、校长,1949年后还是乡村小学的校长,一直到退休。
看到老人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蒋校长。蒋校长思路敏捷口齿清楚,除了听力略差之外,其他方面甚好。
你说我是老革命?哈哈,他笑起来依然那么慈祥。
以下是我从他的叙述中摘取出的一些故事。
193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还是学生的我去镇上买笔墨纸砚。镇有城门,城门口设双岗,由日军把守。按规定进出城门的中国人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我那天戴着帽子,鞠躬时忘记脱帽。日军当即冲上来打我耳光,我被打得耳朵嗡嗡作响,心里又怕又恨。我斜眼望着日本人,以记住这张脸。我之前不懂什么叫救国,但那一刻有了一个质朴的愿望,希望自己今后能为建设国家出力,国家强大了,中国人便不再受此屈辱。
那时候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可我的家乡不仅被日本人蹂躏,还受到战争导致的地方混乱的煎熬。乡亲们都希望能有人来维持社会秩序。
10月的一天,镇上出了一张布告,告示的内容大意是说:他们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有他们在,大家不必害怕,署名周苏平。周苏平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这份布告的作用非常明显,随之不久,有身穿便衣的工作队出没,在村民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平息了日军入侵所造成的混乱。
我16岁那年,进城卖花生,回家路上被汉奸和日军抢了,一分钱都没剩下。那时候我发誓,要穷尽一生寻找救国之路。1941年初,我被新四军推荐到一所小学工作,除了教书,还在老百姓当中开展抗日宣传。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当老师,一当就是一辈子。
1942年1月,组织上派我去苏南四行署干训班学习,那次学习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学员们互称“同志”。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中,每天两粥一饭,早晚餐以萝卜干下饭,午餐两个素菜加一盆汤。虽然吃得简单,可粥菜都弄得清清爽爽。所谓的教室,不过是一间空空的房子,同志们以自己的背包当板凳,膝盖是桌子。参加学习的同志都坐得笔直,如同军人。
蒋校长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问:“韦永义司令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叫司令?”
我小的时候,大人逗小孩玩,常讲“汤司令到,热水瓶泡”,以至于我对“司令”有了警惕心,老觉得除了正经的司令称谓外,其他司令都是“汤司令”。
蒋校长答道:1940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把丹北定为苏南第一游击区,第一游击区建立地方抗日武装丹北独立支队,后来改建为保安司令部,韦永义专员兼保安司令。
蒋校长继续着他的回忆:
在之后的课程中,学员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延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论持久战、反对党八股等内容。开课前我去领“笔记本”,领到手才知是几张白纸,大家将领到的白纸装订成本子。我在这个别致的笔记本上记下的第一句话便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这一生将要为什么奋斗。
我愉快地度过了学习的每一天。眼界开阔了,世界也变得不一样啦,很多困惑和阴霾因为认识的提高而解开。我每天都想大声为这个崭新的世界歌唱——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方。在学习的间隙,我们就唱歌,部队文化教员带大家唱歌,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还有《跟共产党走》等。
一天,课程结束后,忽然,警卫部队一队战士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位消瘦的战士高喊:“同志们,日伪军突袭,大家立刻转移!”小战士往我怀里塞了一样东西,我先以为是棍子,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枪。小战士急促地边说边比划地演示了一下使用方法,丢开我又去教另一位学员。耳边是撤退转移的呼叫和纷乱的脚步声,我定定神,集中注意力按照小战士教的开枪方法演习了一遍(不发射),还想再巩固一遍时,已经有人推了我一把并喊道“快跟上”。
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密集的枪声响起,有子弹呼啸而过。我的心咚咚跳着,我鼓励自己不要被恐惧压倒,革命者是不能被恐惧压倒的。
到一条河边时,上面下了涉水的命令。来不及多想,战士们带着大家下了水。冰破了,河面上腾起水雾。我不会游泳,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跟随着部队战士们往前去。水慢慢没过大腿,到了腰际,最深时到达胸部。浸湿的棉裤棉衣很重,我走不稳,几次要跌进水里,被同伴拽起来继续往前赶。终于过了河甩掉了敌人,这时人人都觉得两腿邦邦硬。原来湿衣裤的很多处已结冰,尤其双腿,像冰柱一般。大家把衣裤上结的碎冰拍掉,继续撤退,绕道路过黑木桥、大成桥、古巷桥,穿过镇常公路,进入丹北山区休整。
1942年2月,我从专员公署结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当校长。战时条件艰苦,教材均是用钢板刻写之后油印。我在教师职业之外,其实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宣传抗日。白天教书,晚上到农民夜校上课、向老乡们了解敌人情况、印发和张贴抗日传单。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丹北山区集中学习一周,交流汇报各校工作情况,根据当前形势布置新任务。在1944年暑假,我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我们做好扩军工作。
我是校长,最清楚学生的状况。我与几位优秀学生谈心,征询他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少年人是激情满怀的,一听参加新四军报效国家,他们兴奋不已。我又做通了家长们的思想工作,送了几位学生参加新四军,他们被秘密转送至苏中公学继续学习。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转业在苏州市任经委主任。另有一位女同学在苏北地区任妇女干部,解放军渡江后留在镇江市区工作。
我前后采访了蒋校长三次,做了近5个小时的录音,蒋校长大部分时间说的都是1949年之前他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斗争、为解放事业所做的一件件事情。我知道那是他所自豪的,让他建立起公而忘私精神之所在。
在采访结束时,我讲起年少时与他的一面之缘。他笑了,说:“原来你就是吃西瓜的毛丫头啊。”
“怎么,您还记得?”
“记得哦,那时我刚退休嘛,看见小朋友感觉特别亲切。”
“我听院子里的阿婆们说,是你耽误了女儿……”
蒋校长笑了:“1960年左右吧,学校有一个老师名额,我那个大女儿呢,样样符合。我家小孩都是农村户口,所以女儿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先人后己,不能有私心,所以将这个名额给了别人。我女儿恨了我好几年。她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最后过得也很好,现在不恨我了。”
蒋校长自妻子去世后,由女儿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他的大家庭非常和睦,儿孙们在各行各业均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