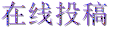常书鸿在工作中
“我是敦煌的痴人!”这是常书鸿的自白。老人活了整整90岁,去世前,他写下了《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回忆和总结——
自我1942年接受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任务,1943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敦煌,还是在异国他乡,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池田大作先生曾问过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这,就是“敦煌的痴人”常书鸿!就是与敦煌已经融为一体的常书鸿!
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赵朴初给他题写的墓碑是:“敦煌守护神”。
学术界的著名大师季羡林给他题写的条幅是:“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女作家叶文玲则称呼他是“民族文化英雄”。——“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乐缭绕,能深刻地感受到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感受到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
与他同甘共苦四十八个春秋的夫人李承仙则说他是块“奇石”,更是个彻彻底底的“杭铁头”。
“杭铁头”是杭州人对倔脾气者——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硬要梗着脖子干到底的人的一种称呼。有关自己的这一个性,出生于杭州的常书鸿却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是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秉性。”——他的祖先是驰骋在白山黑水的女真族。
的确,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更尤其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性格将对他的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封面
为了敦煌,常书鸿选择了回国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曾经这样说过:“父亲生前,更多的人只知晓他是敦煌的‘守护神’、敦煌学者,他也称自己是‘敦煌的痴人’,是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敦煌的人。但是他早年留学法国,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得到美术界应有的关注和了解。”
的确,作为20世纪初即留学欧洲且研习西方绘画艺术的青年画家,常书鸿曾经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33年至1936年间,在巴黎及里昂的春季沙龙和独立沙龙展中,他的油画《浴女》《病妇》和《裸女》先后获得了金质奖章,《D夫人》和《湖畔》先后获得了银质奖章;1936年,他的油画《姐妹俩》则获得了由巴黎美术家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并于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荣誉奖;在此期间,常书鸿还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先后有五幅作品被巴黎现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和里昂市美术馆收藏,且于1935年被评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及肖像画协会的会员……这一切对于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画家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梦寐以求的殊荣。就连常书鸿自己也颇为得意,他不止一次地撰文写道:“连我自己也觉得已经是蒙巴纳斯(巴黎艺术家活动中心)的画家了。”的确,此时的他已经真正进入了巴黎的主流画界。
然而,就在常书鸿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这一艺术的摇篮,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原因无他,仅仅出于一个“偶然”——在塞纳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他看到了被伯希和偷拍的《敦煌图录》;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他看见了被伯希和盗窃的敦煌绢画!


常书鸿、李承仙画作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纳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这一次的震惊,不仅仅是让常书鸿发现了在自己的祖国同样蕴藏着如此精美的艺术瑰宝,更让他第一次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艺术观与艺术追求——“带着卫道者的精神和唐·吉诃德式的愚诚,在巴黎艺术的海洋中孤军奋战,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创作,想用自己的作品来‘挽回末世的厄运’。”就这样,几乎是在刹那之间,他那不远万里跑到西方来寻求“艺术之神”的美梦即彻底地幻灭了。
艺术上的觉醒,进一步带来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似乎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我随着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纳斯地下铁道的站口,一股混合着人体和机器散发出来的浑浊的气味强烈地向我冲来,将近十年了,我在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这样的气味啊!这时,带着疲劳和厌倦的心情,一种难以排遣的浓烈的乡思猛然袭击着我的心。我默默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这一年,是公元1936年。“杭铁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作出了重要的选择。
离开世界闻名的艺术之邦,这对于已经在巴黎稳稳地扎下了根,而且是衣食无忧、家庭美满的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常书鸿不是不清楚。数十年之后,他在接受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采访时,亦开诚布公地承认了这一点——“当时,在繁华的巴黎,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地位。作为里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协会的会员,我过着非常安定和舒适的生活。把这所有的优越生活丢弃,回到祖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到只有流浪汉才去的、荒芜人烟的敦煌去,就更非平常之举了。”
的确,常书鸿所自称的“非常安定和舒适的生活”并非一句虚言——当时前来邀请他画肖像画的大有人在,因为他的那幅《裸女》,被专家们评为“活脱脱是又一位出浴的维纳斯”;当时将他的静物画或是风景画挂在客厅墙上的也大有人在,因为他的画风被诩为颇类于17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本。有人欣赏,就有人购买;有人购买,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于是,他有条件将妻子送去学习雕塑,也有条件将女儿打扮得像童话中的公主;他更有条件住进宽敞明亮的公寓,并以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召集人的身份,将活动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中。1935年,教育部参事郭有守及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李熙谋曾盛情邀请他回国执教,他没有理睬,那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与优越的环境当中。
由此可见,常书鸿为了敦煌而毅然做出回国的决定,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他的妻子陈芝秀百般不能理解,他们争吵过,红脸过,但常书鸿的决心坚定如山:“我的理想,是将来要让全世界的人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让全世界的人像喜欢巴黎一样喜欢敦煌。——但这个理想,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实现!”
如果说,是敦煌的艺术点燃了常书鸿心头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话,那么当他踏上国土后所直面的一切,则越来越加深了他的这一情感。——1936年的东北,已经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列车驶进满洲里,常书鸿竟成为了搜查的对象。箱子被打开,书籍被抄检,远道而返的游子被久久地困在了火车上。1937年,北京也沦陷了,身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常书鸿不得不背起行装汇入到浩浩荡荡的流亡大军之中。一迁江西庐山,二迁湖南沅陵,三迁云南昆明,他跟随着学校饱尝了颠沛流离的滋味。1939年,贵阳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途经此地的常书鸿不幸中了“头彩”,栖身的旅馆被炸成了一个大洞,携带的行装及书画全部葬身火海……那天,幸逢常书鸿及妻女们都不在家,死里逃生的他立即重置了一套画具,《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壮丁行》《前线归来》《湖北大捷》……他用手中的画笔,为灾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发出了呐喊。
作为“敦煌的痴人”,这时的常书鸿时刻都没有忘记远在戈壁沙漠中的莫高窟。侵略者的屠杀和蹂躏,加深了他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一紧迫感与责任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强盗们的掠夺本性的警觉与认识。他为国人开出了一张历年来敦煌被盗的详细清单,他更反复地提醒国人:这批强盗中有洛克济(1879)、斯坦因(1907)、伯希和(1908)、橘瑞超(1910)、华尔纳(1924)等人,他们来自英、俄、德、法、美、日、瑞典、匈牙利等国家,他们“相继诱窃盗取,因而传布表扬,简直把20世纪这个‘发现时代’探险发掘的狂潮从欧洲扩展至亚洲腹地”!为此,常书鸿要迫不及待地赶往那个被强盗们时刻觊觎着的敦煌,垂涎欲滴着的敦煌,以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任……然而一直等到1942年,他才总算盼来了一个机会——迫于舆论的压力,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同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
又是一场家庭的纠纷,又是一场夫妻的争吵。常书鸿再次发起了“杭铁头”的脾气,他丢下妻儿,独自上路了!那天——1943年的3月4日,当他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颠簸,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敦煌,来到望眼欲穿的莫高窟时,他流下了眼泪——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经卷已不复存在,宛如人们搬家以后留下来的一座空房子,感到非常空寂。壁画上的供养侍女和供养比丘尼静静地站在菩提树下。供养侍女的脸上充满善良的微笑,仿佛在向我轻声诉说着什么:“终于把你盼来啦,我的孩子。请你自己看看吧,我很惭愧没有能保护好这满屋子的珍宝。我默默地站在这里,要告诉所有到这儿来的人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那时,我自己也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也要永远站在莫高窟的大地上,使她不再遭受任何灾难和蹂躏。
——这,就是常书鸿立下的誓言。
为了敦煌,常书鸿选择了“服刑”
艺术家最爱幻想,也最多浪漫,尤其是对于长期旅居海外的人来说,竟不知敦煌除了飞天外,还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临行前,友人们曾反复叮嘱也反复告诫常书鸿——
徐悲鸿说:“到敦煌去是要做好受苦的准备的,要学习唐三藏——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经的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于右任说:“在敦煌的石窟中有一幅《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没有看到这幅图等于没有到过莫高窟;到了莫高窟则一定要理解这幅图中的深刻含义。”
张大千说:“在敦煌行使研究和保护之责,无疑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
常书鸿笑了,他称自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回答大家道:
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的工作!
常书鸿先从重庆乘飞机到兰州,然后再从兰州乘卡车继续西行,100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月之久。到达安西县城后,再也没有公路可以通行了,放眼望去,全是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芨芨草,于是只得改骑骆驼,120公里的路程又花去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多少年之后,常书鸿回忆起这段艰难的跋涉,不胜感慨:“离开热闹繁华、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去戈壁沙漠,感觉好像是离开了人世间的生活。”他告诉日本友人:“敦煌位于中国的西部,非常遥远,没有人愿意去。古诗云:‘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回望鬼门关。’其实,敦煌还要在嘉峪关以西四百多公里,是一片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地方,这里在古代是流放犯人、遣派苦役之地,总之一句话,是任何人也不愿意去的地方。”
一路上风沙扑面,一路上饥寒交迫。常书鸿这样描述“冷”的滋味:“在行车途中,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打着面颊,以至双耳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有时还疼得不得了。如果早晨要很早起来出发的话,帽檐上和眉毛上就会结满了冰霜。每个人的面颊都因为天冷而冻得通红……下车时,腿脚早已冻麻木,需要活动很长时间,才能开始走路。”至于“颠簸”的滋味,常书鸿同样难以忘却:“碰到大石头或者小沟坎,卡车就颠晃得很厉害,人几乎有从车上被摔下去的危险,所以大家虽说是睡觉,但还必须牢牢地抓住绑行李的绳子,否则就有可能掉下车去。到了下一个休息点的时候,大家不只是腿脚麻木,手也被冻得通红,都肿了起来。”

莫高窟九层楼
其实,作为考验这才刚刚开始,等到常书鸿终于站在了莫高窟的面前时,才知道一切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么浪漫——“窟前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林。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
至于那里的生活,也是等到常书鸿真正安顿下来之后,才切身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服刑”。——莫高窟宛如一座孤岛,所有的生活用品必须到15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买到。常书鸿凑合着住在了中寺的后庭里,即那处名叫皇庆寺的以前为参拜者修建的庙宇内。没有床,他动手和泥做成土坯,再用它们垒成一个台子,铺上草席,放些麦秸,便成了自己的睡铺。没有桌椅,他同样用土坯垒制,再在表面涂上一层石灰,以求美观。至于照明,则成了常书鸿最大的心患,寺庙的窗户特别小,又没有电灯,他只能在小碟子里倒上点油,以草茎充灯芯,制成了一盏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的“油灯”。
“住”,是如此的简陋;“行”,同样是令人唏嘘——刚开始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直至数月之后才陆续添置了两头驴、一头牛、一匹枣红马,这竟让常书鸿兴奋得像发了一大笔横财一样;至于“衣”,就更不能讲究了——这里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均以老羊皮袄御寒,毫无美感尚且不说,那一股股的膻腥味竟让第二年来到这里的陈芝秀止不住地呕吐起来;谈到“食”,更是一言难尽——莫高窟的水是从30公里外流来的,含有大量的矿物质,苦涩异常,初来乍到的人搞不明白,为什么吃饭时总要和上一点醋,原来竟是为了起个“中和反应”;主食除了土豆便是杂粮,至于新鲜蔬菜和荤腥,根本见不到影子。那年,常书鸿三岁的儿子由于体弱多病吃不下饭,姐姐常沙娜只能四处讨来一点白面,切成方块后于炉子上焙熟,美其名曰“饼干”,以给弟弟解馋……
陈芝秀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常书鸿为什么非要把家安在这里——当年她虽然勉强同意了他的选择,但总是希望能够将家安在重庆,每年往敦煌跑个两趟也就可以了;不曾想,最终不仅是常书鸿自己一去不复返,而且更将一家子人也全都“绑架”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于是,一场家庭的悲剧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45年的4月,陈芝秀丢下了丈夫,丢下了一双年幼的儿女,与他人私奔了,她没有义务在这里陪同丈夫一起“服刑”,一起“发痴”!
这一打击对于常书鸿来说可谓致命矣,数十年后他仍然不能原谅,不能释怀:“这对我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开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尽力找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赶她,可是结果茫然。最后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昏倒在途中,幸而遇见长期在戈壁滩坚持工作的地质学家沈健南和一位老工人,他们救了我,把我护送回敦煌。我面临着生活上的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和严峻考验,像沙漠中的一阵黑旋风那样,遮盖了我前进的光明大道……”平心而论,陈芝秀的出走也实属无奈,生活的艰辛只是一个方面,丈夫将所有的情感都投在了壁画上,这不能不让她感到失落。“一位江南的大家闺秀,一位留法的女雕塑家,能够在莫高窟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坚持了近两个春秋,也委实不简单了。”若干年后,当常沙娜也做了母亲,她才逐渐地理解了妈妈,也原谅了妈妈。
其实,这场家庭的变故也正好为常书鸿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机会——他完全可以回到重庆去,回到妻子的身边。在那里他有一个能够按月领取薪金的“闲职”,也有一个可以自由创作自由挥洒的画室;他还可以卖画,与大后方的其他文人相比,画家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无虞的。但常书鸿丝毫没有动摇,他那“杭铁头”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
在悲痛中,尤其是夜深人静、一片肃寂,九层楼的风铎传来清脆的铃声。我凝望敦煌石窟,便产生了一种幻觉:壁画上的飞天闪着光芒向我飞来,她们悄声向我诉说:“你夫人离你而去,但你决不能离我们而去,决不能离敦煌而去!”
当时,我的良心深深地谴责我:“书鸿啊,书鸿,你为何回国?你为何来到这荒僻之地?坚强起来!心向不同,夫妻难为,本在情理之中。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论前面有多少困难,踏着坚实的大地继续前行!”
据常沙娜回忆,此时的常书鸿创作了一幅油画——《临摹工作的开始》:“画的是少女时代的我和陈延儒先生的新娘(才18岁的敦煌姑娘)。这幅画以石青色调的‘经变’壁画为背景,用笔潇洒自如,着笔在人物的面部,把古代壁画与少女们潜在的青春活力融为一体,表述了画家对敦煌事业的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为什么要为油画起这么一个名字?无疑,它象征着常书鸿的“开始”——一场风暴后的重新“开始”。
就这样,常书鸿继续选择着苦难,继续选择着“服刑”。他在庭院里栽下了一棵又一棵的果树,他将葡萄酿制成了“常氏精制法国葡萄酒”;他既当爹又当妈,还兼当了沙娜的启蒙老师,硬是将女儿培养成了一名出色的艺术家。1947年,命运之神终于为他送来了一位与他一样铁了心要来敦煌“服刑”的女学生李承仙,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她成了他相濡以沫的伴侣。但是残酷的敦煌却让他俩又一次地付出了牺牲——襁褓中的小女儿沙妮夭折了!医生说是软骨病,先天的,病因源自母亲怀孕期间缺少日照。常书鸿和李承仙都哭了,他俩知道这怪不得任何人,只怪自己长年累月地钻在石窟内工作,又哪里能够见到阳光?同仁们将这个可爱的如同小“瓷人”般的孩子葬在了莫高窟的土地上,挽联上的落款是“孤独贫穷的人们敬赠”……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这,就是常书鸿对待命运和苦难的回答。

常书鸿与李承仙在敦煌
为了敦煌,常书鸿选择了坚守
其实对于每一位前来敦煌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考验还不是生活上的艰苦,也不是工作中的艰辛,而是寂寞——远离尘世的寂寞,背井离乡的寂寞。
那是数十年之后的1962年,常书鸿写下了一篇名为《喜鹊的故事》的散文。他说,不久前的一个冬天,一只孤独的喜鹊飞到了他的窗外,这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可真成了一个稀罕物。于是他每天用馒头屑喂它,而喜鹊也成了他的“客人”,一到苦寒季节便准时来到他的窗外等待“布施”。后来,他的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不仅盖起了汽车房,而且装上了玻璃窗。但是不曾想,玻璃屡屡破碎,却始终找不到原因。一天,这只喜鹊终于让常书鸿看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它看了我几眼,忽地一个健步,飞跃在汽车房前,用嘴啄在玻璃上,烦躁地叫了几声,跳来跳去地望着玻璃反光中它自己在杏花背景中的影子,像冬天在我窗外乞食那样,啄一阵玻璃,又飞到树上叫一阵,像要发生什么情况似的。我正在怀疑,说时迟,那时快,一刹那,这只疯狂了一般的喜鹊,忽地把自己的身子,像俯冲轰炸机似地冲击在汽车房的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了,喜鹊惊慌失措地振翅飞去了!”——原来是喜鹊将玻璃中的影子当成了自己的伙伴,就连它也害怕孤单啊……
其实,在常书鸿的身边也不乏愿为敦煌效力的人,愿与他同甘共苦的人——1943年,他初次进入敦煌时,即有五个人斩钉截铁般地跟随着他来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又有数名昔日的学生以及美术工作者相继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尽管也有个别的心怀叵测的“骗子”,抑或自私自利的“小人”——比如说,一个搞摄影的竟把拍摄的全部资料席卷一空,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也把考察后的所有记录窃为己有……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是为艺术而来,是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来。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无所畏惧——仅仅5万元的开办费,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死后能够埋葬在有泥土的地方,不至于像敦煌这样,除了沙还是沙。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们同样勇往直前——以临摹为例,敦煌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洞里不能生火,大家就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工作;洞里没有照明设备,大家就一手端油灯,一手持画笔;洞顶的藻井高达十余米,大家便借助镜子,通过里面的映像进行描摹。
然而,面对孤独和寂寞,他们却难以忍受了——在这个方圆20公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孤舟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既没有社会活动,又没有文体娱乐,更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形影相吊的孤独,使大家常常为等待一个亲友的到来而望眼欲穿,为盼望一封家书传递而长夜不眠。
于是乎,他们终于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那是发生在1945年的冬天,先是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是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一位同仁这样回忆道:“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消息传到千佛洞却是一个月以后的事,闻讯无不欢欣鼓舞,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可是稍一定神,故乡亲人之思就顿时倍增,八年流亡他乡的滋味应该结束了,所以人人都想东归。先是阎文儒走了,苏莹辉走了,大雪纷飞中又送走了邵芳,继之董希文夫妇带着孩子也走了,我当然也急欲回到中原与亲人团聚。潘絜兹家眷在兰州,他当然也要走,于是我俩偕行于1946年初,告别了千佛洞。当时乌密风夫妇正在敦煌县城,他俩听说我们走了之后,自然也是不安于位而东归了。就这样,研究所的专职人员全都走光了……”这一次的打击,委实不亚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常书鸿的心一下子被掏得空空。1948年,他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那种黄羊奔窜、沙鸟悲鸣、日落沙棵的黄昏景象,使我们仿佛体会到法显、玄奘三藏、马可·波罗、斯文·赫定、徐旭生等那些过去的沙漠探险家、旅行家所感到的“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那般的境界。是的,我现在才了解于(右任)老先生的话:“我们这里需要对于敦煌艺术具有与宗教信仰一样虔诚的心地的人,方能负担长久保管的任务。”
这是常书鸿所面临的第三次选择——是去?是留?他仿佛真的具有了“与宗教信仰一样虔诚的心地”。他说,他此时想起了那幅《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萨陲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就这样,常书鸿再一次地选择了坚守,而这一守就是整整五十个春秋!
常书鸿并不是佛教徒,在他的思想深处,既没有佛学的意念,也没有佛学的追求。他说过,敦煌艺术首先感动于他的,并非其宗教的内容,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坚毅、朴厚的优秀性格”。萨陲那太子的舍身精神只是其一,还有那数不清的为敦煌艺术献出了毕生心血的古代画工们,其不屈不挠的身影更是一种力量,一种帮助人们战胜孤独、战胜困难的无形的力量。常书鸿曾作过这样一个对比: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琪罗,由于成年累月地为教堂和皇宫作画,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他的精神被后人写进了美术史,世世代代得以传扬;但是,“在中国,在敦煌的469个洞窟中,该有多少不知名的米开朗琪罗在沙漠边塞中默默无言地完成着他们光辉伟大、流传于世的创作啊!”——这便是常书鸿从敦煌壁画中汲取到的力量。
1948年初,常书鸿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数年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并以此向全国人民进行汇报:清除石窟中的积沙10万多立方米;修建保护性的围墙960米;重新勘察与登记石窟465个,其中彩塑2000多座,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如果将其连接起来,足有22.5公里之长。至于临摹与研究工作,则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历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辑与整理,并且还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于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巡回展览……在莫高窟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对它所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和研究;是常书鸿让它彻底结束了任人破坏、任人掠夺的历史,是常书鸿让它重新闪烁出了迷人的光彩!
然而,就在常书鸿成就了敦煌的同时,敦煌也同样成就了常书鸿——它们不仅使他改变了人生观,也使他改变了艺术观;不仅令他开始了对于民族性格的思索,也令他开始了对于民族艺术的反思。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孤军奋战中的常书鸿写出了一篇名为《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的文章,他将灿烂的敦煌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经过八年来的抵抗,胜利终于来临。在这时候,我们应该计划一下今后的文化建设问题。那站在前驱的艺术动向,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立国基础。我们知道,目前已是“航运”的世界,我们并不缺乏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缺少的是引证历史的实例、找出文化自发的力量。因为只有历史,才能使我们鉴往知今地明白祖国的过去,明白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敦煌艺术是一部活的艺术史,一座丰富的美术馆,蕴藏着中国艺术全盛时期的无数杰作,也就是目前我们正在探寻着的汉唐精神的具体体现。
就这样,常书鸿将他对敦煌的爱,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常书鸿将他对敦煌的痴,久久地伴随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我是踩着九层楼的风铎声走过来的。尤其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仰望深青色的夜空,明月皎皎,风铎阵阵,它们仿佛在责问我:“你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干得怎样了?”……那种凄凉的声音给我以安慰,给我以希望,也促使我振作起来。
——这,就是常书鸿无怨无悔的心声。

常书鸿墓地:面朝九层楼、背依三危山
常书鸿,1904年生。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33岁;进入敦煌的那一年,他39岁。他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拼过刺刀,但是在这场捍卫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尊严的战争中,他同样是一名英雄,一名伟大的却又无名的英雄!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