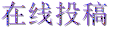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说这段话的人是梅贻琦——清华大学的校长;

梅贻琦
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三年之前,北平沦陷了,天津沦陷了;令世人瞩目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践踏与蹂躏。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三所学校撤出平津,于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仅仅几个月,长沙又危在旦夕,学校不得不请准教育部,再次作出西迁昆明的决定。1938年2月,全校师生带着所剩无几的资产,兵分三路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4月2日,奉教育部令,临时大学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由于校舍紧张,理、工二学院设于昆明,文、法商二学院暂时落脚于蒙自,一学期后迁回本部。
依照最初的协定,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了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并轮流“坐庄”担任常委会的主席。但是没过多久,蒋梦麟和张伯苓即前往重庆另有他任,整个联大的重担便落在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肩上。整整八年的时间,梅贻琦与学校生死相依,休戚与共,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师生们亲切地叫他“梅常委”——他的确成为了校园中名副其实的“常”委!
——这,就是梅贻琦在作上述演讲时的背景:他被逼上了梁山,他更被逼得发出了“不应退却”、“不应畏缩”的誓言。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段特殊的历史,对这所著名的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迄今难以企及的奇迹”,有人将它称为“斯芬克司之谜”。然而“谜”也好,“奇迹”也好,都与梅贻琦的艰苦撑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一支默默燃烧的蜡烛,但蜡烛的本身同样是历史的体现;他是一支静静书写的钢笔,但钢笔的本身亦同样是历史的化身。
……那是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教授亲笔为它题写了碑文:“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缅维八年支持之辛苦,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他一共为其列出了四条“可纪念者”,而这四条“可纪念者”,不仅是联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也是梅贻琦个人的自豪。
可纪念者之一——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的确,西南联大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西南联大的胜利与民族的胜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它的精髓,就是民族气节,就是爱国主义!——有了它,才能“与抗战相始终”;有了它,才能产生出“旋乾转坤之功”。此前,三校的历史虽然各不相同,但爱国主义的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的。以南开为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校长张伯苓即向全校同学号召道:“设因此次事件,刺激特深,武人能因之彻底团结,青年能因之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诚堪为中国前途庆幸……余不以此指望全国青年,但望我南开同学共奋勉之!”作为张伯苓的弟子,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的国难纪念会上亦高声呼吁:“沈阳既去,吉林、黑龙江、锦州随之而陷。大家不要以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时敌方时时可以再有动作,或另有阴险图谋,实则形势非常可危。吾们应当深刻纪念,时时注意准备才是。”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精神,三校师生才有可能辞别故土转战他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精神,梅贻琦才会挺身而出,承担起繁重而艰巨的校务。然而昆明并非世外桃源。战争给西南联大带来的威胁,首要的便是空袭,惨绝人寰的空袭——
其中最为惨重者有三次——1938年9月28日,设于昆华师范学校内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军事教官及其5岁的幼子当场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毁,办公处与教员宿舍多处震坏;西仓坡清华办事处中二弹,两名留守人员当场殉职。1941年8月14日,校园中弹70余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饭厅多处被毁;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实验室被炸;图书库中弹;常委会办公室及出纳组、事务组、训导组、总务处被夷为平地……
此时,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与大家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其夫人回忆道:“西南联大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开躲起来。月涵(梅贻琦的字——笔者注)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陈岱孙教授的描述就更加具体了:“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席地坐于校舍北门外的乱坟之间。飞机临头时,一起跳入乱坟中事前挖好的壕沟里,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的确,在这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梅贻琦梅贻琦的一举一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除了镇定自若,除了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外,更要代表学校向世人控诉日军的暴行,向民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告校友书》上,他勉励大家道:“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为此,在整整八年的时间内,西南联大从未因为躲避敌机的轰炸而停止过办学。为了避开空袭较为集中的午间,学校将上课的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如果再碰上警报,则索性将课堂搬至山坡上或是荒野中……
战争给西南联大带来的第二个威胁是贫困——
由于国家经济惨遭破坏,教育经费只能按七成拨给,教师的薪俸也只能按七折领取。以学校而言,每月的拨款只有三万余元;自1938年4月起,教育部再次从中扣除百分之三十,作为“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不久,又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也宣布停付,学校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不得已,只有借贷,但是,五年间的欠款连本带息已高达1400万元,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六七十年才能还清。为此,学校的一切开支只能从简——房屋以黏土打垒,房顶以铁皮覆盖;不曾想一旦下雨,声响如鼓,教授们只得于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大字,成为了联大的黑色幽默。然而等到1941年,就连这铁皮屋顶也不得不拆下拿去换钱了,“停课赏雨”竟成为“绝响”……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深感对不起大家,他“开源”无路,只能“节流”——下令撤去了办公室的火炉,更主动封存了学校派给他的汽车。
以教师的生活而言,同样是吝囊羞涩,饔飧不继。数学大师华罗庚栖身于牛圈的棚顶上,文学大师朱自清身披赶马人的毛毡以御寒,物理教授吴有训的皮鞋露出了脚趾头,著名诗人闻一多捕捉蚂蚱以果腹……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与大家一样囊空如洗。夫人于大街上摆起了地摊,变卖孩子们穿不下的衣服,再后来索性和其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卖起了自制的糕点——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取名为“定胜糕”。做成后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为了省钱,总是步行,往返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结果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梅贻琦默默地看着妻子,不知该怎样安慰是好,他只说了一句话:“今后出门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别人知道你是校长夫人又有什么关系?——我梅贻琦没有当亡国奴!”
人们说,这就是联大的精神;联大人说,这就是他们的骄傲!梅贻琦为这所诞生于炮火中的学校制定出了新的校训:“刚毅坚卓”。——四个字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刚强不屈,坚定不移。为了鼓舞士气,梅贻琦又于全校征集新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字里行间抒发的是同一个精神:收复河山,报仇雪耻。一校之校训,体现出的是它的办学思想;一校之校歌,体现出的是它的办学精神。这校训与校歌,成为了梅贻琦的精神支柱,也成为了联大人的精神象征。
在这样的一种激励之下,联大的教师们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坚守三尺讲台,坚守文化阵地。他们明白,一个民族的教育事业是维护和发扬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精神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冲锋陷阵,不亚于攻城拔寨。联大的学生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祖国而学习,为抗战而服务。那是1943年,为了协助援华的美军开展工作,梅贻琦亲自动员学生们投笔从戎,担任翻译。——“‘国家……民族……难道中国的青年不敢为着他的祖国冒点危险吗?’梅贻琦先生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像铁锤似的打击着我们。”这是当年学生们的回忆。为了勉励更多的学子参军,梅贻琦作出决定:四年级的同学,服务两年后不再回校,以毕业论;四年级以下的同学,复员回校后免修一定的学分,以资鼓励。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一共有多少学生奔赴前线,如今已很难统计清了。有人说1100人,有人说1600人,但有一个名字是不会错的:梅祖彦。他是梅贻琦的独生子,那年才满19岁。
的确,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可纪念者”,就是它的“与抗战相始终”。——是它,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显示出了崇高的气节;是它,让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展示出了巍然的风采。
可纪念者二——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抗战爆发后,为了解决高等院校的办学问题,国民政府曾批准建立了西北、东南、西南等多所“联合大学”,但是除了西南联大外,其余的“联合者”没过多久便解体了。究其原因,似乎并不难解,这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反之,能够存在下来者,能够“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者,倒是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
文人相轻,自古有之;再加上政治倾向性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要想把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学校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无疑需要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一开始,三校之间确实有些貌合神离——“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这是后人为之作出的总结。然而没过多久,这一“格格不入”便彻底消失了。不仅三校教授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联大校政交梅校长主持,我们放心!”而且其他两位校长也对梅贻琦充满了信任——张伯苓说:“我的表你戴着。”(即“你代表我”之意)蒋梦麟说:“我的不管就是管。”
梅贻琦上任了。但是从他的性格来看,似乎并不具备“领袖”、“舵手”一类的魄力——他不爱说话,人们称他为“寡言君子”。然而了解他的人明白,他的魅力恰恰就蕴藏在了这一“寡言少语”的背后: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的表现,正是他礼贤下士的体现。八年多来,他有似一位高明的指挥家,默默地却令庞大的乐队奏出了和谐的乐曲;他有似一位精湛的美术家,无声地却令多种的色彩组成了绚丽的图画。

第一,尊贤敬能。
1931年,梅贻琦初掌清华大学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大师论”,正是梅贻琦执掌联大的思想核心。正因为他尊重知识,尊重贤能,才会有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汇集于他的旗下——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吴宓、王力、金岳霖、汤用彤、潘光旦、华罗庚、陈省身、吴有训、曾昭抡、吴大猷、周培源……真可谓群贤毕至,众才咸集,西南联大被世人誉为了“教授储备库”。梅贻琦又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他有过这样两个比喻:一是说自己是“率领职工为教授搬椅子的人”,二是说自己是京剧中的那个看似气派却并非主角的“王帽”。在他的日记中,年年月月都有着同样的内容——遇有生病者,亲自去探望;遇有结婚者,亲自去贺喜;遇有丁忧者,亲自去吊唁;遇有贫困者,亲自去襄助……尤其是后者,他不止一次地召开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而且更屡屡地“久卧不能成眠”。古语曰:“士为知己者死。”有这样的掌门人,各路贤才又怎能不“襁至而辐辏”?
第二,求同存异。
梅贻琦不仅能够将诸多的大师级人物招徕而来,而且更能够将他们长久相留和睦相处。个中原因不在别处,就在于他具有宽阔博大的胸怀和“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思想。在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存在着种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一是不同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的人,能够共事于同一系科,甚至开设同一门课程。比如中文系的罗常培、刘文典,他们视新文学如洪水猛兽;朱自清、沈从文,则是高举新文学大旗的著名作家。他们的观点形同水火,但在工作中却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二是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乃至不同党派者,也同样能够相安无事,甚至成为朋友。后人曾列出过这样一张名单:校园内既有左派政党者、民主社会党者,也有无党派而经常批评政府者及持中立态度却又对政府有意见者;既有国民党、三青团人士,又有他们中的反对派与批评派……这一局面的形成,关键在于学校为之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而作为第一把手,梅贻琦的宽厚与包容,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三,一视同仁。
在联大的三位校长中,若论资排辈,梅贻琦无疑居末。然而张伯苓也好,蒋梦麟也好,为什么都那么信任他,这便是缘于梅贻琦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和舍己为人的品格。有人这样分析: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清华占了绝对的优势,因此这份家务确实不好当——“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以领导层的安排为例,梅贻琦始终考虑到三校的利益,绝无孰轻孰重之分。以教师的安排来看,为了避免清华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他校的优势,梅贻琦没有将其全部放入联大的编制内,而是利用清华的庚子赔款基金,建立了国情普查、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等研究所,将“多余”人员分散其中。在其他方面,梅贻琦也同样是一碗水端平,充分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例如,为了解决教师生活上的困难,清华大学曾利用其工学院的设备,成立了一个服务社,以创收的钱款来补助同仁们的生活。这事本与其他二校无关,但梅贻琦照样是一视同仁,年终分红时同样赠予北大与南开的教师们一人一份“奖金”……
的确,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可纪念者”,就在于它那“八年之久,合作无间”。——有了它,则可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不再是“一盘散沙”;有了它,则可向国人骄傲证明,知识分子永远是“团结抗日”的模范。
可纪念者三——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当年,朱自清在一篇名为《清华的民主制度》的文章中这样评价梅贻琦:“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毛子水亦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若着眼于文化的更可贵的一方面,则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至少,依我个人的意见讲,这件事情比培植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价值得多;因为这是人类精神修养的一种最高贵的表现。”
这,也就是冯友兰在碑文中所提出的第三个“可纪念者”——西南联大不仅树立了“学术自由”的精神,而且具有着“民主堡垒”的称号;这里的人们不会随千夫之“诺诺”,只会作一士之“谔谔”。
西南联大的自由与民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大学独立”的理念,二是具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当年,北京大学就曾以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而著称,南开大学亦以从严求实和活泼创新而闻名,至于清华更是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无疑,这一切正是西南联大的“自由”之源头、“民主”之基础,同样它也是“现代大学”的精华之所在、命脉之所系。以清华大学的管理模式为例,梅贻琦自掌校后,即全力扶植这一校长组织协调下的教授治校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设立教授会、评议会以及校务会议等三个不同的机构。——“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它的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科研以及学风等方面的提案;审核学生的成绩并授予学位;建议评议会讨论的事项以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选举评议员,推荐各院院长,并从教授会中聘任教务长。“评议会”则是这个体制的核心,它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选举出来的七位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教授治校”的作用便是通过它的职能而表现出来。“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及各院院长组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机构。
至于西南联大的体制,陈岱孙总结道:“不能说梅贻琦先生把清华体制引进了联大。但在联大,一个类似清华领导体制原则的确认和梅实际上主持联大常委会不是没有关系的。”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下,教授于学校中具有了至高无尚的地位和权力。而这一体制的施行,更是从根本上摆脱了国民政府强加于它的种种限制与束缚。——那是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公开向“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主张提出了宣战:“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贯通。”“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于是西南联大同所有学校一样,被强行贯彻了一系列的“部订”规章制度——课程表、教科书、教授的资格审查、教师的聘任和待遇,乃至行政机构的设置等等,都要按照国民党的“部颁标准”执行。此外,他们还在联大成立了“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以及训导处等等,以此来控制师生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1941年前后,更明确规定了担任院长以上职务者必须加入国民党,以最终达到“以党治校”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只有两种选择:其一,站在政府当局一边,对师生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严厉的管制;其二,站在进步师生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学术的制度进行坚决的抵制。梅贻琦不是警犬也不是奴才,他不会选择第一条道路;但梅贻琦也不是左派不是斗士,他同样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事实证明,他有着更为有效的办法和更为有力的武器——这就是那个足以体现“大学独立”与“教授治校”精神的教授会和校务会议的制度。有了它,则可以“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有了它,则可以进行有理有利的抗驳。比如说针对那个“部颁标准”,他以校务会议的名义,向教育部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再比如强令加入国民党一事,作为校长,他本人不能不“遵命”,但是对于其他的教授,他则“无权”干预了。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务长杨石先当面拒绝:“这一席位我可以马上辞去,入党之事断不可为!”这样的回答,无疑是以“大学独立”的精神为力量,以“教授治校”的制度为后盾。至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师生所下达的逮捕令,又或是强令安插训导长的企图,更是被梅贻琦以“学校一切大事均由校务会议决定”为挡箭牌,一概不予理睬。为此,西南联大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成为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别的学校几乎都被国民党操纵于手掌之中,唯有它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坚固堡垒。对外,它抵抗住了一切干扰与压力;对内,它保护住了进步的师生,并营造出了一片民主与自由的新天地。
“大学独立”与“教授治校”的意义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方面,朱自清在文章中这样总结道:“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这“谁都有一份儿”,正是西南联大最终收获的成果:教授们不仅是主人,更是公众人物,他必须处处为人师表,时时率马以骥,并以此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那是1941年,为了解决部分教师的贫困问题,教育部明文规定,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可以领取一笔“特别办公费”。但是在西南联大,各院的负责人均公开表示放弃,梅贻琦不仅带头,而且连教育部下发给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四个正在联大读书的孩子去享用。反面的例子也并非没有,中文系的刘文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是非混淆,善恶不辨,不仅投靠了地方上的大土豪,而且严重贻误了教学工作。中文系开除了他的教职,一向宽厚仁慈且求贤若渴的梅贻琦同样没有宽恕他。
在这样的一种追求之下,一种“风气”之中,西南联大能够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是不足为奇的,更是“可纪念”的。——正是因为有了它,方显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如何捍卫着民主与自由的权力;正是因为有了它,方显出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如何吸取着“现代大学”的精华。
可纪念者四——
“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
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冯友兰于纪念碑的碑文中“稽之往史”,他说: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四次偏安“南渡”的耻辱,前三次均“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但是第四次,也就是西南联大的这次“南渡”,却一反前例,“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胜利地返回了故土。作为联大,这确实是它的第四个“可纪念者”;作为梅贻琦,则终于实现了当年他所立下的要把这艘“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的船胜利开回清华园的誓言。
其实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恢复之全功”的学校并非西南联大一家,因此冯友兰所说的“可纪念者”应该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容——这便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这两句话来自美国的一所大学,在清华30周年校庆时他们发来了贺电。这十个字意思既简洁又深远:西方经过了1000年的努力才出现了一流的“现代大学”,但是在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足以与之相媲美的高等院校。的确,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收获,才真正是西南联大的骄傲——
从办学的规模来看:战争中三所学校的损失均惨重之极,但是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西南联大即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着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及1个先修班和1个进修班的综合性大学了;在校学生达3000余人,以八年累计,共毕业2522人,这于当时国内的高校来说,可谓首屈一指。
从科研的成果来看:八年期间硕果累累,仅以获得重大影响的著作而言,即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补校》;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王力的“语法三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吴晗的《明太祖》;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汤用彤的《西汉魏晋佛教史》;潘光旦的《优生概论》《自由之路》;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它们于国内外无不具有领先的水平。
从培养的人才来看:八年期间从西南联大的校园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学子,这里有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这里有八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郭永怀……;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81名院士,西南联大占了25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出470名学部委员,西南联大又占了其中的118名……
无疑,这同样也是梅贻琦个人的骄傲。今天的学者是这样提出要求的:“作为一个高等学府的领导人,只有具备大教育家的素质,才可能把大学办出一流水平。”对于梅贻琦的评价,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了他对西南联大的领导上,其实如果深入地分析一下他的办学思想,他是真正具备了这一“大教育家的素质”的。他不仅具有优秀的领导才华,更具有成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第一,他提出了“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
梅贻琦认为,大学不应该“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因此对于学生来说,首先应该进行的是“知类通达”的训练。其次则是“人格”的全面培养,即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意志品格和修养情操。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一,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以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开阔他们的求知视野;其二,允许学生在校内组织各种社团和活动,以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活跃;其三,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与调查,既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又服务于社会与民众。
第二,他提出了“教授治校”。
梅贻琦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由此可见,他所倡导的“教授治校”,其含义不仅在行政管理上,也在教书育人上。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一,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以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开阔他们的求知视野;其二,允许学生在校内组织各种社团和活动,以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活跃;其三,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与调查,既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又服务于社会与民众。
第二,他提出了“教授治校”。
梅贻琦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由此可见,他所倡导的“教授治校”,其含义不仅在行政管理上,也在教书育人上。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对“慎选师资”是十分重视的,其当选者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其一,要学贯东西,通晓古今,并且于学术上兢兢业业,居于领先的水平;其二,要治学严谨,教育有方,能够启思设疑,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西南联大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基础课程,包括各专业课的“绪论”,均由著名的教授来担任。原因是只有他们才能深
第三,他提出了“学术自由”。
梅贻琦说:“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学校里的每位教师均“自由”地而又努力地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且不断地充实与完善。陈寅恪在讲授隋唐史时即公开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有着这样的自由与自信,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八年中教师们开出的课程多达1600门,足以给学生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二是呈现出了“百家争鸣”—校园中“教师沙龙”、“Seminal”(讨论会)等活动层出不穷,正如学生们所形容的“谁也不怕谁”,它使各种学术在争论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梅贻琦成功了!他不仅使自己成为了“大教育家”,而且让西南联大“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让中国的教育实现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学子们称他是“永远的校长”;同仁们誉他为“中西合璧的真君子”。——是的,正是他的这一成功,令世人了解了教育工作者于文化抗战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正是他的这一成功,令世界知晓了中华民族拥有着傲视天下的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