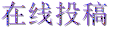劳榦曾经这样描述陈寅恪的相貌:“……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徐葆耕曾经这样形容陈寅恪的性格:“屠格涅夫认为人性有两极:一极以堂·吉诃德为代表;一极以哈姆雷特为代表。……以深思忧郁而论,陈寅恪是接近哈姆雷特的。”
——对于这样一位有着甘地的气质、哈姆雷特的性格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16年、精通十余个国家的语言、且广泛涉足于佛学、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教授,毛泽东赐予他的评价是“国宝”,同事们赠予他的称呼是“活辞书”,学生们给予他的赞誉是“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说过这样的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则慨叹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战争——生灵涂炭的战争从天而降时,他所受到的伤害也就最深最重。贾植芳曾经这样总结过:“……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
——这一年陈寅恪已年近半百,这一年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对于这样的遭际,陈寅恪曾写下两句诗:“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上句表明了他于战争中的立场,下句表明了他于战乱中的无奈……

陈寅恪、唐筼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残剩山河行旅倦 乱离骨肉病愁多
战争爆发之前,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并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开设了“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唐代西北史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一系列的课程。据说当年—即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刚成立时,在是否聘任陈寅恪的问题上,梁启超与校长曹云祥曾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没有任何学位。”曹又问:“他有无著作?”梁答:“没有任何著作。”曹摇头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可就……”梁生起气来:“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但著作算是等身了,然而全部加起来却还顶不上陈先生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先下手为强吧!”曹一听,竟然连外国人都如此推崇,当即便签下了聘书。
就这样,从来不为“学位”而读书的陈寅恪回国了,并以“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的身份跨入了令人仰慕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他是第四位受聘者,其前还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此同时,名声大振的陈寅恪还受北京大学之邀,为其历史系的学生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聘请,兼任其研究员及历史组主任;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聘任,出任其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时的陈寅恪可谓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于学术研究方面,进入了他的黄金阶段;于生活方面,亦步入了最为富足、最为安定的时期。
罗香林这样回忆陈寅恪的授课——“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教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而其风度和声音笑貌,也最为学生所神往。”
蓝孟博这样回忆陈寅恪的学问——“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先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
然而,1937年的这场罪恶的战争,却无情地击毁了这一切——包括陈寅恪那从容的治学和怡然的心境!
陈寅恪的一家是于1937年的11月3日撤离北平的:先乘火车至天津,再坐轮船到青岛,最后又换火车一路南下,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汉口……直至11月的20日,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湖南长沙;在这里,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了“临时大学”。这一路上,陈寅恪没有留下日记,但他的家人们却有着这样的回忆——夫人说:出天津东站时,“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岁,小彭7岁)。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在济南车站上,“人满得挤不上车”,“幸亏刘清扬先生眷属已先上车,帮助我们每个人由窗口爬进。他们还让给我们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容易。”女儿流求则记得,为了防止走散,父亲让她背熟了沿途的所有站名以及相关的人名和地址……
但是不曾想,长沙并非他们流徙的终点—数月之后,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的征程。固然,这是特殊的战争年代,在这特殊的战争年代中,像这样的颠沛流离也并非陈寅恪一家。但是他与别人不同,妻子体弱,孩子年幼,因此甫抵香港即先后病倒。先是夫人心脏病发作,继是小女高烧不退,全家不可能再继续一道前行了。为此,陈寅恪只得独自一人赴昆明,而将病妻与弱女留在了举目无亲的港岛上。但是又不曾想,云南的“瘴气”同样没有放过陈寅恪,他也被击倒了。两地的相思,同病的相怜,茕茕孑立的陈寅恪在凄冷的病榻上吟出了这样的诗句:“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当年同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钱穆,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39年的寒假,他独身一人隐居在宜良北山的岩泉寺中,潜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状不禁慨叹道:“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此时的钱穆,家眷同样不在身边,但是陈寅恪的牵挂却要比他沉重得多——毕竟香港不同于内地,更毕竟妻女们如今是“寄人篱下”。长女流求曾这样回忆她们滞留于香港的日子:“父亲的薪水为旧国币,不断贬值,寄到香港后,换成港币很难维持生活。”为了节省开支,她们曾先后六次搬家,而母亲和妹妹的病,更使她束手无策:“三妹将满周岁,染上百日咳,昼夜尖声咳嗽,足足折腾了三个多月,此后她更加瘦弱。……母亲病情最危重的时刻,由许地山伯母协助才住进医院。我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那时刚满10岁,虽然心里害怕,可并不懂事,也不知该做些什么事……”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非得神经病不可”的原因——他不仅鞭长莫及,而且是无力相助。
好在机运总算眷顾了他一次——那是1939年的春天,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他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教授。以前陈寅恪曾坚定地表示过:“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但是这次他却迫不及待了,他给校长梅贻琦写信:“弟于牛津教书实不相宜,故已辞谢两次。后因内子有心脏病,不能来昆共聚一地,种种不便,……故不得不试为一行,其实为家人可共聚一地计也。”“现中英文化协会虽借款300镑作路费,但须偿还,且不能过久。现内子在港医药即挪用此款,故弟更不能不去英矣。”——一向清高孤傲的陈寅恪,终于向现状“折腰”了。
然而,命运却又偏偏多舛——1939年的暑假,当他前往香港奔走办理全家人的护照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航路中断,英国之行成为泡影;1940年的暑假,他再次赴港等候机会,驻英使馆却送来了这样的通知:“应聘之事须延缓一年。”然而,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恰于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镇南关失守,陈寅恪被阻隔在香港,进退维谷了。
为了养家糊口,陈寅恪只得临时就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学校和住所相距甚远,一个单程就得花去两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就连这样的日子也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敌手!由于消息中断,大后方的师生们竟一时不知陈寅恪的下落,在西南联大的壁报《论坛》上,甚至出现了《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一直到了1942年的5月,在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和西南联大的共同努力下,总算为陈寅恪筹集到了三万余元的路费,陈寅恪这才终于逃离陷城,与家人一同返回大陆——13岁的大女儿记得登上轮船后的情景:“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风巨浪使轮船左右颠簸,多数乘客都晕船卧倒。”年仅5岁的小女儿则记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
九死一生的陈寅恪实在是疲惫不堪了——位于乐山的武汉大学请他去讲学,他谢绝了;位于李庄的中央研究院送来聘书,他退回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久劳之后,少息之余,愈觉精神疲倦不堪,百病转发,心跳不眠等症,渐次复见,又有瘰疬及目眩之病。”于是他在桂林落下脚来,只为能少受一些旅途的劳顿。小女陈美延回忆道:“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人住的房子可能还有几个铁马钉用于梁和柱间的加固,茅草顶的厨房可就一颗铁钉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风雨袭来,我们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大风把厨房的墙吹倒,大家庆幸当时没人呆在厨房里。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余时间就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张小木凳了。”陈寅恪则以诗句中记述了他的心情:“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局就连这样的生活也没能让陈寅恪继续过下去——1943年的夏天,战火逼近广西,他们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逃难的旅程。当年的美延虽然年幼,但她却终生难忘一路的困苦与艰辛:“母亲在路上得了痢疾,病情严重,到贵阳就无法再走了。而我也不时发烧,晚上就由父亲照顾我这个病孩子。……后来父亲也病了,等母亲稍好,我们又继续上路向四川进发。到重庆父母接连生病,不能成行,跟着二姐和我出麻疹,出疹后我又得了个泻肚不止的病。总之全家轮流生病,好不容易才到了成都。”……学生蒋天枢和蓝孟博得知老师抵蓉后立即赶来探望,但他们看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幕:陈寅恪一脸病容地斜靠在榻上,却一眼瞥见了他俩手中拎的三罐奶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探起身来:“我缺乏的就是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给陈寅恪带来无限伤害的战争!它令满腹经纶的学者漂泊无定,它令月薪480元的教授买不起一罐奶粉!陈寅恪终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他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沧海横流无处安 藏书世守事尤难
其实要说苦难,流离失所也好,贫病交困也好,这对于一名学者——尤其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来说,都还不算是最致命的;战争所给予他们的最大伤害,应该是“藏书世守事尤难”。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书;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同样离不开书:购书、读书、教书、写书……当年在清华园时,陈寅恪的学生们无不记得:“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他的晚辈们也清楚地记得:“寅恪叔购书成癖,毫不吝惜。……每年春节琉璃厂市集期间,他总要去逛旧书摊,一去就钻到旧书摊中流连忘返。”为了读书,他13岁即出国留学;为了读书,他直至39岁才想到结婚成家……
战争打响了,清华园外炮声隆隆,清华园内的陈寅恪仍在潜心读书——他在比较“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与“欧阳竞无之唯识学”在解释佛经时有什么区别,他更在孜孜矻矻地与同仁们展开争辩。就连吴宓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到钦佩:“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1937年的7月28日,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独自一人住在清华园中的陈寅恪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随着大批的难民逃进城内,与家人相守在姚家胡同3号的寓所之中。生命是无虞了,但他却放心不下书房中的那些未能转移出来的书籍和手稿。侄子陈封雄则当仁不让地“奉命于危难之间”了——“总算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我乘车去抢救。慌乱中,我只能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一车。汽车刚要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经过检查,一看都是线装书,就放行了。当时日本飞机仍在西苑投弹。以后清华大学成了日军兵营,寅恪叔的《大藏经》和其他许多书就不知下落了。”据陈封雄回忆,这套由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的《大藏经》,是当年他跟着陈寅恪一同去购买的,价格2000多元,几乎花去了他数年来的全部积蓄。
然而作为损失,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与后来陈寅恪屡屡遭受的劫难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二次是在逃离北平之前,由于携带不方便,陈寅恪便将自己常用的一批书籍交给邮局寄运,不曾想这一决定竟为他酿成了终生大祸——“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这是陈寅恪于文化大革命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虽然这些并不属于他的“罪行”,但从中可以窥见数十年来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陈寅恪来说,他真正的损失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书的本身,平时他有一个习惯,即读书时必须做到“三到”:眼到、心到、手到——凡是有所得抑或有所疑者,立即提笔注在书页周围的空白处;等到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等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辟独到的论文。蒋天枢曾亲眼见过陈寅恪的这种“蓝本”:“寅恪先生生平读书,有圈点,志其行文脉络腮理;有校勘,对本校或意校其伪误;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俊,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因此这一次的损失,对于他来说,已不仅仅是书籍本身了,更有他的“心得”以及诸多文章的“初稿”。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有想到,第二次的打击尚未平复,陈寅恪又遇到了第三次灾难,而且以“价”相论,更是远远地超过了前者。——嗜书如命的陈寅恪对其所藏之书颇有三六九等的划分:遗留在清华园中的那一批,虽说珍贵无比,但非经常所用者;通过邮局寄运的那一批,虽说须臾不可离,也不是最为重要者;他的珍爱,全都放在了随身所带的行李内,与他一同从北平来到长沙,从长沙来到香港……但是不曾想,他又大意了!——那是1938年,他从香港取道越南去昆明,为此而特意买了一只高级皮箱以装载他的手稿和书籍,并交火车站托运。哪知该时的滇越铁路交通混乱,小偷猖獗。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竟被小偷误认为藏有贵重财宝而受到“光顾”。
窃贼得手后大失所望,但陈寅恪的损失却非同小可——箱子里装的都是有关蒙古史、佛教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的书籍,而作为它们的“眉注本”,作为研究者的“半成品”,这次的罹难,则令计划中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五代史〉记注》《巴利文〈普老尼诗偈〉译注》《〈蒙古源流〉注》等许许多多的著作再也无法问世!夫人唐筼告诉他人道,这一时期陈寅恪“几乎得了神经病”。——他的心被人挖去了,他又怎能得以平静?
然而,令人扼腕的故事还在继续:那是到了1955年,这批被以石头“调包”的古籍竟然出现在了越南西贡的书肆上。华侨人士彭禹铭购得其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但是由于越南政府禁止图书出口,不久彭家又遭遇兵火,失而复得的它们最终还是化为了灰烬。
当然,经过这几次的损失之后,陈寅恪也并非空空如也——在他的手边还幸存一部带有眉批的《通典》。于是1939年他便据此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并随后寄往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命运之神竟再一次地与他作对,陈寅恪第四次遭遇到了不幸!——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部书稿转交香港印刷厂印刷,但是战火临头,整个工厂连同陈寅恪的心血被一起葬身于火海之中!……今天,人们在书肆中所看到的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部同名的书籍,已非原来的定稿了,而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大力相助,用他以前的一些旧稿相凑而成。一向严谨的陈寅恪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喜?是忧?是谢?是嗔?他只能反复叮嘱自己的学生:“恐多误。”
有人曾经拿钱穆和陈寅恪相比:二人同从北平逃亡,但钱穆却会动脑筋,专门制作了一个带有夹层的箱子,致使书籍随身携带没有任何的损失;二人同将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钱穆却小心谨慎,亲自赴沪办理,致使他的著作能够顺利出版……这究竟是性格的原因呢,还是命运的使然?陈寅恪真是倒霉透顶了,他在诗句中写下这样的心愿,而这样的心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
他想的仍然是“书”,梦的仍然是“书”,但是战争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这一切,终于使得原本藏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学者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

陈寅恪故居
流转西南 致丧两目
再退一万步讲,书籍的遗失也好,手稿的失踪也罢,它们毕竟都是身外之物;如果再加上双目失明,不能读书,不能写书,这对于一名从事研究的学者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偏偏都让陈寅恪给碰上了!
战争爆发之际,陈寅恪的右眼因为视网膜剥离已经失明了,但是他却毅然地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夫人一道带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以及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了逃难的历程。稍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眼病是不能劳累的,是必须立即治疗的。但是陈寅恪为什么急着要走,甚至等不及父亲陈三立的出殡?原因无他,只是不愿多作一天亡国奴。
在吴宓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9月23日:“2:00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先见登恪,后见寅恪。寅恪述病及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适矣。”
老舍于城陷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面对敌寇的入侵,陈寅恪说出的也是完全相同的内容:“为全节概而免祸累!”
陈寅恪出身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宁陈氏”。这个家族不仅辈出文化名人,而且以坚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祖父陈宝箴,入京会试时,恰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遥望其冲天大火而击案痛哭,并毅然放弃科场进取,投身军旅,以身报国;父亲陈三立,得悉有人散布亡国言论,怒然相斥道:“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为此绝食五日,忧国而逝……因此,陈寅恪是背负着国恨与家仇上路的——这时的他又怎会顾及到自己的眼疾?又怎会顾及到眼疾的进一步恶化呢?
关于陈寅恪的右眼,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因为父亲慷慨赴死,致使他悲痛过度而失明;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平时看书太多缺乏休息,而终致伤害……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上路时只是病其一眼,至于最后两眼双双失明,他自己的结论是:“流转西南,致丧两目。”
那是1944年的初冬,已经来到成都且于燕京大学教课的陈寅恪,一天突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不曾想没过几天,悲剧竟发生了!——那是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醒来之后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人们都说“久病成名医”,右眼的病变应该使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剩下的左眼:第一不能受到磕碰;第二不能用眼过度。但是自逃亡以来,由北平而长沙,由长沙而香港,由香港而昆明,更尤其是后来那桂林、贵阳、重庆、成都的一路颠簸,一路劳顿,又怎能保证左眼不再继续受到损伤?而且每到一地,只要稍一安顿下来,他便急不可耐地要看书,要工作——抵达成都仅仅一年,他就写出了《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11篇论文,以及《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的主体内容。昏暗的灯光,过度的疲劳,他的左眼又怎能保证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当年正在中学读书的陈流求,清楚地记得——“期末考试评卷后,要把分数及时无误地登记在细小的表格内,父亲实感视力不济,极其无奈,只得叫我协助他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粘合视网膜的手术是在成都存仁医院做的,吴宓不仅经常去看望老友,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1944年12月18日:“探寅恪病。今日下午左目将行割治。筼夫人在侧。”12月19日:“往存仁医院视寅恪,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多,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12月21日:“探寅恪病,甚有起色。……筼阻寅恪勿多言劳神,宓遂辞出。”12月23日:“探寅恪病。仅见筼夫人,言寅恪又不如前,不消化,失眠等。”12月24日:“探寅恪病,转佳。筼夫人议,欲得宁夏产而在宝鸡可购之枸杞子煮汁,制糖膏,或以羊肝及羊胎、熊胆等食寅恪以益VitaminB1B2,而使寅恪身强,血多,目明。”12月28日:“探寅恪病,方眠。筼夫人言,昨夕医言割治效果不佳,致寅恪大忧戚烦躁不安,日来健康又损。”12月30日:“探寅恪病,方食。后筼夫人送出,秘告:医云,割治无益,左目网膜,脱处增广,未能粘合,且网膜另有小洞穿。寅恪未知此层,已甚焦烦云云。”……就这样,手术彻底失败了。在医疗技术和医学设备都不能保证的战争年代里,医生们不仅无法让陈寅恪重获光明,而且还将他的视网膜弄皱,致使后来赴国外治疗时,亦无力回天了。
陈寅恪的精神被彻底击垮。他还有多少壮志未酬,他还有多少著作未写——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宏愿:撰写出一部能够超越《资治通鉴》的《中国通史》,再撰写出一部令世人警觉的《中国历史之教训》。早在住院之前,他给李济和傅斯年写信道;“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如今当这一悲剧“不幸而言中”时,他只能留下这样的诗句了:“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病榻上的陈寅恪确实是悲凉之极,学生们怜惜自己的老师,自动组织起来轮班陪护。王钟翰这样写道:“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所费甚昂,维生素B价亦不赀,且不易得。陈师母(唐筼女士)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蒋天枢则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按语”:“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是啊,假如能有“如果”的话,陈寅恪完全不至于双目失明——如果当年他不急于离开北平,如果后来他不拼死逃出香港,如果……不是曾有人于陷城之中给他送来了急需的大米?不是曾有人于失业之时高薪聘请他去主持“东亚文化协会”?但是陈寅恪全都断然拒绝了—他不会接受这“嗟来之食”,更不会接受这“嗟来之职”。
当年身陷香港的情况,他曾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傅斯年——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北京大学’亦来诱招,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20万(港币40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弟虽回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但他也真的是坚不附逆;他明白如何保持文人的气节,他更明白如何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邀,前去讲授东方汉学。在座的中国女教授陈衡哲这样评价他的学问:“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的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的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实可惜陈寅恪再也看不见讲台下的这一切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如果没有书籍的遗失,如果没有双目的失明……那么,他的学术研究又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他的研究成果又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
——陈寅恪,1890年生,1969年去世。抗日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他55岁。具有着甘地气质的陈寅恪、具有着哈姆雷特性格的陈寅恪、具有着“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之博学的陈寅恪,实是中国文人中的一个典型。他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所受到的苦难——作为“国宝”级的人物,战争对于他的摧残,也是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摧残;他的意义更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他始终没有倒下,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坚守着“文人”的岗位。是的,还有谁的磨难比他更深呢?还有谁的成就比他更高呢?失明后的他,照样讲课,照样著述,照样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系列叹为观止的著作。无怪乎他的助手黄萱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文人的气概;它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

黄永玉填写的陈寅恪的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