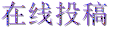谢作林(1945年10月)
1948年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7月25日我的父亲谢作林旧伤复发,在前方野战医院(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肖郭庄)救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父亲33岁,我还不到两岁。
父亲1946年6月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又说是侦察营)营长。现仍健在的王昊叔叔回忆说父亲牺牲时任华东野战军先遣支队副支队长。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定格在几张发黄、缺损、保存了60多年的老照片上。照片上的父亲年轻、威武,一身戎装,两眼炯炯有神。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照片上抽象的父亲慢慢变得鲜活起来。
父亲谢作林(祝林)1915年正月初四生于江西省宁都县安福区朱源村一个雇农家庭,爷爷谢华清生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老三。一家人终年忙碌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父亲小小的年纪便在心中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30年,15岁的父亲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第二年和他的两个兄长参加了红军。父亲在第三军团特务团机枪连当战士。1932年1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父亲作战勇敢,多次负伤。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父亲因负重伤未能跟随主力部队长征,自此投入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所在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从此他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直至抗战胜利,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父亲是怎样打鬼子打老蒋的,我一无所知。
听母亲说,1946年中秋时节,我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村庄。我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在挑夫的箩筐中、在行军中度过人生最初岁月的。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带我到一个村庄,我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从一群身着军装人们的缝隙中向一个躺在床上的人看着,然后听到了吹号声,人们就向一垛土墙走去。这就是我最初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一直相随至今。以后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记忆,小时候晚上睡觉,母亲常搂着我含着泪水小声吟唱:“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三岁二岁死了娘啊……”我在母亲绵绵的歌声中进入梦乡。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二十军要赴朝作战,母亲准备将我送到外婆家。她问我跟妈妈还是到外婆家,我毫不犹豫地说跟妈妈!就我这一句话,母亲下了决心:为了我这个烈士的唯一后代,她忍痛脱下了军装。临转业前,爸爸红军时的老领导、老乡贺敏学把他的一把小手枪和一床缴获来的羊毛毯送给了母亲。当然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在我成家时母亲把羊毛毯作为纪念品交给了我,手枪已在“文革”初期上交组织。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地印在我脑海深处。

1950年母亲储秀英和儿子谢伟年在嘉定留影
我和新中国所有的孩子一样,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直到“文革”初期,因造反派要抄我的家,而我对造反派扬言“谁要抄我家,我就和谁拼”的情况下,母亲担心我出事,找到她的老上级——二十军第一任军长刘飞伯伯,想把我送到部队。刘飞伯伯二话没说,拿起电话接通了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的谢云辉叔叔说:“我这有一个烈士的儿子要当兵,你要不要?”“烈士的孩子我要,叫他来找我。”就这样,1968年春我当兵了。入伍前母亲才把父亲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1958年,母亲带我回江西宁都老家。一路火车、汽车到达宁都后,由县委派通信员带路,步行60里山路,才到达安福区朱源村。通信员把我们母子带到村口水塘边一座很旧的老屋前,只见一个矮小硬朗的老人手扶在门口在向我们张望,这就是我的奶奶!母亲拉着我快步上前,年近70岁的奶奶右手拽着母亲,左手紧紧搂着我放声痛哭,许久许久才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谢家有后了……”我一直跟母亲储秀英姓储,为什么说“谢家有后”?我不明白(直到我入伍时才改跟父亲姓)。
这时村民们奔走相告来了不少人,把天井挤得满满的。原来,解放后我和母亲是第一个回村的。泪水在奶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一个劲地流淌,她像树皮似的粗糙的手不停地在我脸上身上轻轻拍打着。我虽年幼,但隐隐约约还是感到大人们有什么事一直瞒着我。看着奶奶和母亲像在交谈,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我要保护奶奶和母亲……直到入伍前母亲才告诉我,当年和我父亲先后参加红军的两个伯伯自从随部队长征后就一直没了音信,也不知是何时牺牲,在哪牺牲。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清剿”,留在家乡的红军亲属男丁无论老弱都被杀害,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我不知道孤苦伶仃的奶奶是怎样度过白色恐怖艰难岁月的。
母亲还告诉我,1944年她在“苏浙公学”妇女队学习并任班长,经妇女队指导员朱虹介绍,1945年9月新四军北撤时,组织上批准她与我父亲结婚。从结婚到1948年7月25日父亲牺牲,两人在一起相处连一个月都不到。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却越来越浓。
1968年月12月我从南京军区坦克教导三团训练结束,分配到广州军区坦克独立三团。临行前我给刘飞伯伯打电话告别。刘伯伯要我在部队好好干。话语虽简短,但前辈们的殷切期望我懂。我总觉得父亲的在天之灵一直在注视着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决不辜负革命先烈对我的期望!1969年底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知道后高兴地流泪了。1970年提干后任团作训股作战参谋,1975年8月任广州军区坦克独立三团营长。
1975年初夏,母亲带着我和爱人一起去山东聊城莘县肖郭庄寻找父亲的墓。在战争年代的老党员、老房东王福才、肖遵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庄稼地边,只见一座高出地面一米多用砖瓦砌成的长方形的墓很显眼地坐落在庄稼地中间。散在庄稼地里正在劳作的乡亲们得知是烈士的亲人来看望烈士,都放下手中的农活围拢过来。从1948年到1975年这27年里,父亲的墓在乡亲们的维护下完好无损,老乡们每年清明都给父亲扫墓。他们对烈士的深厚感情至今想起都感动不已。1982年,时任团参谋长的我在父亲生前的老部队第二十军和莘县民政局的帮助下,将父亲的墓移到了聊城地区莘县丈八烈士陵园。
1998年父亲牺牲50周年。我和爱人一起去山东聊城给父亲扫墓。当走进简朴庄严的丈八烈士陵园,我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手中的花圈在颤抖,我在心中默默地念着:父亲,儿子来看您啦!站在父亲的墓前我感到我的心与父亲靠得是那么近。此时此刻,我记忆中的父亲,我照片上的父亲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微笑着,前辈们向我讲述父亲的战斗经历又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显现。
是啊,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父亲是其中的一员!我为有这样一位永远年轻的父亲而自豪!而骄傲!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63岁的儿子向33岁的您敬军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