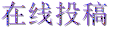金一南在十七大小组会上发言

金一南在国防大学学术报告厅
2013年12月24日晚,刚下班回到家,就接到赣州军分区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金老师在赣州,并把电话转给了金老师。电话里传来金老师那熟悉的声音。赣州军分区政委给他讲述了我2009年去赣南、闽西调研时听到红军、苏区的故事泪流满面的事情,我告诉他我到解放军报社工作两年后的第一本作品集《心灵的坐标》下月出版,金老师嘱咐我“好好努力,近期成绩不凡,不要懈怠”。
回想离开老师两年多的时间,我撰写发表了100多万字的稿件、上千幅图片,发布了长达200多分钟的视频。那些走边防、上高原、下海岛的艰难采访路,特别是连续两年新春走军营在界碑巡逻路中双脚韧带撕裂、部分跟腱撕裂、踝关节积液、骨髓水肿的那些日子,我的眼前是金老师做手术后趴在地板上写作和在波涛汹涌的战舰上完成了《苦难辉煌》一书创作和修改的艰辛,还有什么能比他难?
我对文字的敬畏,并非始自到报社工作,而是在2006年金老师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产生的,即使多了一个“的”、“地”、“得”、“着”、了”、“过”,他都不会放过,这让我感受到了他治学与为文的严谨。我对工作的敬业与执着,也同样来自老师的言传身教。他在国防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就把全军各大单位都调研了一遍,有时买不到卧铺票,他就在硬座下面铺一张报纸,爬到底下休息一夜,这就是老师给我做出的榜样。
2010年,我去赣州军分区讲课,还去了金老师父亲金如柏将军的故居——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至今道路依旧颠簸、泥泞。站在那个小菜园,看到那老旧的房子,想着当年金如柏将军就是从这里跟着红军出发、用一生践行自己信仰的主义,不觉内心涌起深深的敬意。他们两代军人心中是共同的理想,他们见证的是弱小的党、弱小的红军、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过程,那一刻,我在那菜园里的绿色中悟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2011年,解放军报社为纪念建党90周年组织的红色足迹万里行,我到了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那里我看到了金老师母亲郑织文女士的名字。她16岁就从河南奔赴到这里,去了她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花季少女编织的青春梦想是救亡图存,绝不当亡国奴。而今已经近90岁高龄的郑织文女士还依然读报、读书,为金老师讲课搜集素材,这不仅是母子情深,更是两代人情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映照。
回望历史,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金老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下了:“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可复制。在金老师的心中,军人的不变追求是“除了胜利一无所顾,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因此,他把自己的文集名字定为《军人生来为战胜》,而正是军人的这种铁骨脊梁和求胜意识,才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风破浪会有时”。
《苦难辉煌》一书,倾注了金老师十几年的心血,他说,完成书稿后,尽管那些英雄都已消失在了历史的帷幕之后,但他的眼前却还是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时浮现。他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4条线索做了2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站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十字路口,每一次交锋,都是血与火的考验。回顾每一个生死关头的历史选择,他得出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历史的自觉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了辉煌。
金老师说:“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核心是放弃。舍得,不舍安能得?”那么,他是如何取舍的呢?他在自己1993年出版的《竞争: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一书“寻觅力量”一章中写了“泥球与铜球”的寓言故事:一个小孩想通过颜色来区分泥球与铜球,可是两个球涂着相同的颜色。一位老人告诉孩子看哪个重,哪个就是铜球。孩子分不清哪个重。老人说:“那就把两个球用力撞在一起,就会分清了。”泥球被撞得粉碎,孩子抱走了他想要的铜球。
这则寓言故事让我陷入了沉思。金老师在他的保险柜里给我取这本书的瞬间,我看到柜子里大小不一的荣誉证书,塞了整整一层。他办公室简陋,办公桌椅陈旧,但这增辉的一大排鲜艳的荣誉证书却被他锁在保险柜的角落里。荣誉证书尘封在金老师的记忆中,40年的军旅生涯,他守住了一颗宁静的心。“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凡是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地去学一门。”他的生命就像一支箭,义无返顾地射向了他选定的目标,想做的是无穷的,但能做的是有限的,我心中的两个球也猛烈地撞在了一起。
金老师的心里思考的都是学术问题。我问金老师怎么做到这样豁达。他问我:“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公平的是什么?是时间。你能抓住的是什么?也是时间。时间为你所用,你就可以做时间的主人。当你把时间浪费掉的时候,那是最可惜的。”当我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最伤自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往往不是敌人,也是自己。要增强自愈能力,削弱自伤能力。要让眼泪与努力溶合,而不是与气馁融合,泪就没有白流。”他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平静、淡定和从容,因为支撑他的是信念,而他依靠的也是自己。自信人生两百年,不管人生得与失,他都守住了心中的那块净土。2008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快到11点了,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内心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我和爸爸战友来到他的母校——国防大学,在月夜下散步。走到国防研究系,我们看到一幢楼只有一盏灯亮着。驻足,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站起来。“金老师”,我脱口而出。“他也是我的老师”,1943年出生的爸爸的战友,望着1952年出生的金老师充满敬意。我们谁都没再说话,一直望着那扇窗,注视着那盏灯、那个微驼的背影。虽然那个身影相比整栋楼是孤单的,但我们的心却和他在一起,这一幕像油画一样深深印在了我心上。
每当我走过金老师的窗前,那盏灯都使我想起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和皴裂的十指,还有那青筋暴露的双手、双臂。他是学者,更像武夫。在他去西藏考察时,我意外接到他的电话,他想给我买护身符。高原反应使他喘着粗气,他问我的属相是兔子还是牛,我说:“兔子。”他说:“好,那就兔子了。”挂了电话,我流泪了。尽管每次我出去调研、采访和讲课,他都鼓励我“好好体验”,但他的心里却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牵挂。我真的好想对他说:“老师,其实您就是我的护身符,有您的支撑与支持,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和闯不过去的关口呢?”
金老师说过:“你今天哭泣,明天会为今天的眼泪感到好笑。挫折是经历,经历是财富。要点燃内心的光明。人就是这样炼出来的。”师从金老师,我从博士读到了博士后,从军事思想专业跨到了国家安全战略专业。很多人问我:“你一个看起来连安全感都没有的小丫头,怎么搞得了国家安全战略?”我说:“我的安全感来自我的导师——金一南教授,因为他被称作国家安全这艘大船‘桅杆上的瞭望者’,有他瞭望,我永远不会迷失航向。”
金老师很少赴宴。不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但每次讲课后他获得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让我理解了他“吃简单的饭,讲精彩的课,做更多的事”的精神境界和“除了胜利一无所顾,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不变追求。2013年“八一”建军节,他在自己新出版的《心胜》一书中写道:“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这与海明威“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异曲同工。
金老师写了《苦难辉煌》,他自己也从苦难走向了辉煌。这是军人的足迹,也正如他每年“八一”都会发给我的不变的短信:“终生不悔是军旅,风雨不倒是军旗!”
坚强的老师从未在我的面前落泪。我在听到刘和刚唱的《父亲》那首歌后,就与金老师一起听这首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讲述了自己当年学英语时,父亲每个周末都把刊载在《电视周报》上的英语教程给他留好,哪怕是生命到了最后,也不愿意他请假回来照顾,但是,却会经常拿出来孩子们写回家的信看,抚摸着孩子们的立功喜报,仿佛远方的孩子就在身边。我在这首歌中深刻地感受到金老师心中对父亲的思念与深沉的爱。
2011年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时请到了金老师当工人时的师傅,见到自己的师傅,金老师老泪纵横。金老师常讲,人生中关键就是几步,而他在人生中那最关键的几步中,师傅给他的指导使他受益终生。难掩激动之情,金老师唱了《共青团之歌》,那是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他唱得仿佛回到了当年。他说那个年代尽管春天里满是泥泞,但人们依旧热血沸腾地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依旧喜欢苏联那些振奋人心的歌曲,那是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一种追求。
金老师随海军编队出访到夏威夷,他执意要去看张学良将军的埋葬地,因为他牢牢记得张学良的一句话:“我是个爱国狂,国家要我的命,我立刻就给,要我脑袋,拿去就可以。”忘我的爱国情怀,永远是金老师做事和做人的脊梁骨。他写过《那一顶耀眼的军人桂冠——记战将粟裕》一文,“当和平时期数十年如一日、每晚就寝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当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扎进裤腰”。这段话让我想到他自己,他的笔记本电源线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他的军装衬衫从来都是扎在裤腰里,他的军装袖口、扣眼儿和裤腿都磨起了毛边儿,因为他穿得最多的就是军装。
金老师先后去过美国、英国、以色列、日本、希腊等国访问、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每次出访前他都精心准备,出去后就尽可能多走访外军院校和军事基地,了解军情动态。在以色列参加会议,他坚持要去充满危险的戈兰高地。在希腊开会,他不去会议组织的爱琴海旅游,而是自费去看伯罗奔尼撒古战场。途经法国,他对逛街和购买奢侈品毫无兴趣,而是专程去看了拉雪兹公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
在国内,他的身影也不在名山大川,而是在东海的春晓油气井、西北的塔里木盆地油气田、东北抚远三角洲的东方第一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疆的南疆、北疆边境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对这些既艰苦又蕴含风险的实地考察,他着迷一般重视。他说:“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绝不能只坐在办公室看文件、看报纸和写材料,必须去到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一线亲身体验。只有深刻感觉到的事物,你才可能真正深刻认识它。”我想起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柏格森以巴黎凯旋门为例说:“如果给你100张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远景、近景、全景、局部和各种细部,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5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金老师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中获得的理性思维,成为他学术素养的根本依托,也成为他做人的根本依托。
2006年5月22日,是我第一次在国防大学指挥员班的课堂上见到金老师。他早早就站在讲台上调试多媒体课件。好一个精彩的开场白,他从“现代危机本身的高变异性和低预测性”引入“危机挑战权威、危机侵蚀权威、危机需求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理论,从1999年美军轰炸我驻南使馆到中美撞机再到“9·11”事件,思维逻辑缜密,条分缕析。
当多媒体课件打出“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老师”时,他在讲课的最后引述了原军事科学院李际均副院长的话:“决策机构需要一批高度爱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丰富实践经验、善于思考又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干部队伍,才能担此重任。”当他抬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时,凝重的神情和他发人深省的课,让“军人”二字站立起来。
2006年,当金老师出海遭遇暴风雨时他拍摄的DV被大浪砸在军舰的钢玻璃上,真是触目惊心,但他却笑着说:“舰身摇晃最厉害时,晕船的老鼠都从甲板里摇摇晃晃爬出来往海里跳。”他没有告诉我他有多累,但与他合作《一南军事论坛》的主持人孙利告诉我,美国时间凌晨一点多,在晃动的军舰甲板上,金老师蹲在由两名记者用雨衣撑起来的狭小空间下,通过海事卫星连线做节目,大家都听出了他声音的沙哑,但他却没有说自己有多疲惫,而是捕捉到很多官兵坚守岗位的细节。他讲述的新闻令在场所有人都肃然起敬,感觉他更像一名职业记者,而且是极具敬业精神的军事记者,那时真正的军事记者都已经撑不住了。连线结束,大家为金老师落泪了。
金老师在节目中讲了从战士到干部的辛苦,却没说他在远航的军舰上为官兵们的三次授课:穿过第一岛链时,他讲了“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入夏威夷军港前,他讲了“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与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在美国西海岸圣迭哥结束军事演习后,他讲了“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他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参加远航,但官兵们最大的收获却是在军舰上听到了金老师的精彩授课。
2006年岁末、阖家团圆之时,国防大学教授办公楼内只有金老师办公室那孤零零的灯光。他为海军出版的编队远航摄影集写前言。室内温度很低,又赶上他发烧、流鼻涕、咳嗽,套上几件御寒的衣服坐在桌前,他的心里还是那梦牵魂绕的远航:
“耳边响彻的是舰艏与浪涌的沉重撞击声、撞击之后舰体的余震和颤抖声、飞溅的浪花被大风加速后枪弹一般击打在舷窗玻璃上和舱壁上发出的爆裂声和屋内各种东西的位移、磕碰声;即使不晕船也消耗巨大,即使疲惫至极也难以入眠——躺在床铺上就和躺在浪木上一样,每个人都拿出独特招数尽量减小自己身体在床上的来回位移。这是大海给我们的重大考验。我们互相惦记、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我们的军舰、我们的官兵通过了这一最严峻的检验。再也没有这样的风浪,让我们如此深刻地感到:我们是事业的共同体,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这就是我们的风雨同舟。我是一名陆军军官,参加这样的远航,遭遇这样的风浪,经历这种身体的、精神的、心理的考验与磨炼,确实受益无穷。当我们跨越万里大洋、穿越惊涛骇浪进入别国军港的时候,当双方的国歌分别奏起、双方军人互致军礼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怎能不油然而生,怎能不衷心感谢我们蒸蒸日上的祖国、我们日益强大的军队。”
没有丰盛晚宴,他在清冷的办公室内用充满深情挚爱的激扬滚烫文字作为自己的新年盛宴。有句格言说:“吃苦最多的人,埋怨最少”,金老师说,“晚间睡在珍珠港内军舰的狭窄铺位上,感觉比睡在五星宾馆的席梦思上还好。一是连续航行18天,第一次获得靠岸那种平稳的感觉;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阵阵海风中凝视舷窗外的夜空,想象当年珍珠港战场的搏杀。吃这些苦换来的对一个军种的感觉、对远洋战略的感觉、对国家利益拓展要求我军具有新军事能力的切实认识,绝非书本、文件、报告所能取代。”43天远航,成为他34年军旅生涯的珍贵记忆!他点燃了自己内心的光明,这光明也照亮了我的军旅人生路。